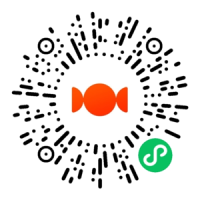你的大脑和手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界限?
编者按:如今,网络生活和 「现实」 生活越来越没有界限,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即使不是我们生理上的一部分,也几乎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本文译自 Theguardian 原标题为 「Wher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your phone and your mind?」的文章。

▲ 手机本身和整个科技革命的影响常常让人无法抗拒。摄影: 埃米利亚诺 · 庞兹(Emiliano Ponz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边界线是明显的。这些边界线常常用来区分不同的两件事情。在法律、物理意义层面,边界线用来指示一件事情的结束和另一件事情的开始。例如我们常常提到的财产边界、身体边界、城市边界等,未经允许就越过这些边界都是违法的。但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却不是这样的,它正在提高边界线的不确定性。我们这才刚刚要了解这会导致什么情况。
曾经有一个思维实验探讨的是人的 「自我」。「自我」 的边界仅指身体形态的极限?还是包含了远在外太空也能听见的人类声音?还包括散布在数字空间的个人行为数据?还包括活跃在几十个不同的社交媒体网络的你?
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随着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康涅狄格大学哲学教授、人文研究所所长迈克尔 · 帕特里克 · 林奇(Michael Patrick Lynch)说:「哲学家安迪 · 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 · 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在 1998 年提出 「扩展自我」 这个概念」。
安迪 · 克拉克和大卫 · 查尔默斯认为:从本质上说,思维和自我会通过一些设备来帮助我们完成认知任务。例如,最平常的一张纸和一支笔可以帮助我们记住一些本来应由大脑记住的任务。平时购物清单的使用便是利用这个原理。

▲ 「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亲密的一部分。」 照片: 美联社
林奇说:「如果这种概念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思想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前沿。依照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我们通过手机来扩展 「自我」,因为手机、智能手表、ipad 等数字设备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们已经完全离不开这些设备。」
智能手机和纸的本质区别在于:我们与手机的关系是互动的(我们不仅将信息输入设备,我们还从设备接收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手机比购物清单更加积极地参与我们的生活。
购物清单不会根据我们过去和当前购物行为来建议我们现在应该买什么,但是手机可以。
林奇新书(The Internet of Us)的开篇用一个思维实验来解释这个边界是多么的薄。大脑能力的显著延伸就像有个设备把智能手机的功能直接植入你的大脑,然后你便掌握这些功能。当前,我们的生活与此并无太大差异,即使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不是我们生理上的一部分,但它们几乎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
Flurry 公司 2017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每天花 5 个小时在移动设备上,人们 2017 年花在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应用上的时间比去年增长了 69%。各种应用程序(Apps)的流行使得我们摆脱了通过浏览器访问互联网的旧观念。世界通过新闻、社会媒体、娱乐等与我们时刻联系在一起。
哈佛大学的作家兼初级研究员莫伊拉 · 韦格尔(Moira Weigel)在撰写她的书《爱的劳动:约会的发明》( Labor of Love: The Invention of Dating)时发现:2009 年,随着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平台的兴起,人们的网络身份慢慢从线上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她指出网上约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社交平台常常是恋爱到约会的过度平台,人们常常会在观看对方的 Facebook 简介或者 Instagram 之后,才决定是否和他们一起出去。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网络身份已经成为了我们重要的一部分。
韦格尔说:「对许多人来说,90 年代或本世纪初的网络空间更多的被认为是一个藏在电脑里的虚拟空间。而当前最大的改变是消除人们对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间的边界感」
关于随时和世界保持联系对我们以为着什么的讨论还处在初级阶段。人们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然而,这些即将消失的边界带来的结果并不含糊,拥有技术的人正在积极倡导和促进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在我们利用智能设备访问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设备的互惠性,其他人也在访问和窥探着我们。可怕的是,有些人会利用智能设备骚扰别人。例如,泄露他人裸照、透露别人的隐私、在网上抨击别人等。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知道技术制造商、应用程序或浏览器公司跟踪并指导我们行为的程度。最近,这个问题在 「剑桥分析丑闻」 事件更加凸显出来。韦格尔认为苹果、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微软、Facebook 和亚马逊这五大科技公司追踪我们对智能手机和浏览器的使用情况,无限制访问我们的数据是合法的。至于民主问题,这些公司利用技术将无数的财富、权力等交给了少数人,而这小部分人则通过调整产品代码来影响数十亿生命。
韦格尔说 「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人同时掌握着高度集中的权利,他们并不公开透明,也没有民主监督,这便是民主程度不足的根本来源。我们已经让许多私营企业接管许多公共功能或公共产品,比如让谷歌成为世界图书馆」。在美国,智能设备大肆侵蚀民主和社会商品的观念,大多数人都做好了让私营公司掌握这些公关权利的准备。
iPhone 巨大的影响力让人很难想象它才仅仅问世十年。尽管手机等智能设备以及整个科技革命常常使人不自觉失去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但是当我们了解用户数据,还是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固这条边界。

▲ 史蒂夫 · 乔布斯在 2007 年展示了新款 iPhone。摄影: 保罗 · 佐久间(Paul Sakuma)/ 美联社
提姆 · 黄(Tim Hwang)是旧金山的一位作家和研究者,他曾担任谷歌全球公共政策领导,从事人工智能和机器研究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思考这些设备如何在个人之外培养集体的功能。他解释道:十年前,网络上的言论是人们会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现在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相对优质的平台,如维基百科,都需要大量的人事管理,才能使平台正常工作。因此,人们给予平台自我调整的权利(允许 Facebook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别的方式。
黄问道:「有没有什么工具或者设计能使网络平台有更好的自治能力? 我们希望给特定的用户更多的限制吗?网络平台是否希望赋予用户更多的权利来控制骚扰和抨击言论?平台是否希望用户知道在哪些情况下,自己的信息被过度使用?」
韦格尔认为限制五大企业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有两个机会。第一种方式是合法的,她引用了许多的研究来探索反垄断诉讼,旨在解散这些公司。布鲁克林法学院法律副教授 K· 萨比尔 · 拉赫曼(K Sabeel Rahman)在维格尔创办的《逻辑写作》(Writing in Logic)中写了许多关于现在经济中缺乏民主和平等的文章,他将他们做出的努力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分裂实业家的努力进行了比较。拉赫曼写道:「既然科技产生了新的权力形式,我们也必须创造出反补贴公民权力的新形式。我们必须建设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实行新的制衡。」 另一个方式是让许多以理想主义而非经济动机进入科技行业的工人帮助规范和限制自己的雇主。以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 · 哈里斯为代表的科技行业人员开始对他们创新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特别是在人类技术创新方面。但是,维格尔对于这种方式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些人常常习惯性使用自上而下思维方式。
第二种方式还是有一些正面的例子。比如今年六月,谷歌(Google)员工发起运动,要求谷歌停止与五角大楼 Maven 项目的合作(这个项目能提高军用无人机的效能)。
韦格尔笑着说:「当你阅读最近六个月的《纽约时报》,你会发现许多技术反弹发生在这五个公司。其实,这些大公司雇佣了数十万员工,其中的许多人不一定同意公司所做的一切。我认为现在工程师们对公司接下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康涅狄格大学哲学教授林奇还认为,我们最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教导人们如何使用智能产品。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公司如何运作、如何跟踪我们的行为,如何根据我们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为向我们提出建议。我们需要理解真实行为与数字领域行为之间的根本差异(尽管边界被侵蚀,但这种差异仍然存在)。
林奇说:「谷歌向你发送一系列问题,你认真填写(例如认证信息等)。这之后,我们便逐渐在互联网上建立我们的身份,但同时,这些信息也会被售卖出去。」 网络世界与现实在结构和运作方面太过相似,这常常使我们忽略我们的数据在被收集和售卖。比如,手机上的应用程序精准地记录了我们同别人的互动、我们的用户信息。
林奇说:「Facebook 等社交媒体总是能通过算法向你发送你所关注的事情或朋友的动态,以此来加固你的在线身份。这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跳动在屏幕上的消息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经常出现在你的社交网络上的朋友,会让你认为这就是你的好朋友。」
本文来自 36 氪,编译为刘麦麦 Jane,爱范儿经授权发布,文章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爱范儿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