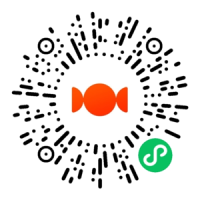部落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去。”但是对于此时此刻创造历史的人来说,却很难以置身事外的心态来面对日常迅疾发生的事,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的说法:“我们再也不能扮演读书识字的西方人那种超然物外和脱离社会的角色了。”原因在于“电力时代,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靠技术得到了延伸”,我们深度参与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回溯人类的故事,部落的发展曲线似乎是从以亲缘关系主导逐渐过渡到信仰主导,再到如今的技术主导。与前两者相比,技术主导离我们最近,也给我们的感受最深。从机械时代身体的空间延伸,到电力时代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建立在电力的基础上),媒介逐渐由单一的工具演变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工具本身是媒介,工具产生的内容是媒介,甚至思想也是媒介。
信仰主导的部落,与其说是对宗教的崇拜,不如说是对语言的崇拜。皇权时代的“皇帝诏曰”,“昭告天下”也是如此,由于技术的落后,语言这一媒介的掌握更多体现在工具本身上,皇帝由于地位特殊性掌控了发布渠道。《邹忌讽齐王纳谏》中,末尾段: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无论是面刺,上书,还是谤讥于市朝,都需要经过“寡人”才具有效用。
科技发展至今日,工具已经不是作为主要的限制了,即便是国内仍然有微博,微信等平台能较大满足信息自由传递的需求,但是崇拜似乎没有根本性改变。正如前文所说,媒介囊括了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思想,电力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媒介的威力成倍增加,对新时代部落的人而言,已经不可能是简单的语言崇拜,而更多体现在语义崇拜。
我们以于建嵘的一条微博为例:
朋友给我传来了这篇《美国人为何不会还中国的钱》,据说这是美国欧洲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总裁彼得•希夫的一个演讲。我看后,想了许多。各位看完后会有什么感想呢?
如果看过彼得•希夫的演讲视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条微博基本上是把对方最敏感的话与阴谋论的观点夹杂在一起的,然而底下的评论并没显示出评论者对事实的足够兴趣,更多的是借这一语境发表个人的观点:所谓借尸还魂了。
麦克·卢汉在抨击戴维·萨尔诺夫将军梦游症的声音(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时说:
(萨尔诺夫)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包括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直接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
语义崇拜主导下的部落在政治热度的渲染下,常常有着不可预知的破坏力,在蝙蝠侠 3 中,贝恩的那句“we give it back to you… the people. Gotham is yours”仿佛哥谭市的潘多拉魔盒,诱使人们对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反抗得到了最大释放。
透过表象,我们无从对任何玩弄语义的一方指摘什么,原因在于这本身是技术主导下不可逆转的潮流,而技术延伸所至的我们都是原罪。
快餐文化也是如此,新技术产生的新媒介,新媒介诞生了新内容,当以怀旧的心态对现实表示出不屑一顾时,不过是“文人在广告环境中苦苦挣扎时夸下的海口:‘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不理睬广告。’”
尽管趋势是如此,但我们也不得不目睹发生在当下的剧烈反差:从一种极端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而这种趋势,也体现在了现今部落文化的发展状态。
文末,我想以村上春树《国境之南,太阳以西》的一段话结束:
回过神时,政治季节已然结束。一度仿佛足以摇撼时代的巨大浪潮也如失去风势的旗一般颓然垂下,被带有宿命意味的苍白的日常所吞没。
部落的变迁,其实与政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