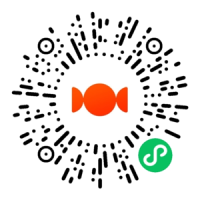2013:我们的新闻理想
今年六月的一个平凡午后,我坐在美国华盛顿新罕布什尔大道与弗吉尼亚大道交界处的一座小咖啡馆里,随手翻阅着当天出版的日报。窗外不远处的波托马克河在初夏的暖阳下静静地蒸发,几步之外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如同在每个寻常白天一般空荡孤寂。在我头顶上方笼罩着的是一座占地 4 万平米的马蹄型堡垒,兀自盘踞在雾谷街区的一角,悄声压迫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它就如同一头怀抱着某个惊天内幕的巨兽一般沉默——当你走进露天中庭之后,抬头只见得方寸蓝天。
四十年前这里的确藏着一个秘密,在被《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公之于众的同时也成就了二人的名噪一时。自从 1972 年 6 月 17 日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手下的安全顾问詹姆斯·麦克考德(James W. McCord)闯入建筑被捕的那个深夜开始,这里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心中的圣地。
欢迎来到水门建筑群(the Watergate complex)。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水门综合大厦其中一栋写字楼第四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长桌的尽头坐着在华府政治圈里享有盛名的白宫记者 Major Garrett。他一边嚼着手里的芝士披萨一边分享着他的选战报道经验和与白宫媒体班子打交道的细节,其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这句:“如果你要报道发生在屋(the House)里的事情,到山(the Hill)上去。听各种各样的议员们都在嚷嚷些什么,得到了确切消息之后再拿回到屋里同他们求证。(注:“屋”指的是白宫,“山”指的是国会山,下同。)不然的话,你能拿到的就只有大堆大堆的白宫新闻通稿(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这里是全美著名的政治类刊物 The National Journal 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也是我在短短一周之内的第二次来到这里——我的导师 Niraj Chokshi 正是 The National Journal 的财经记者。
坐在同一张会议桌周围的还有十几个我在乔治城大学夏季学期“政治新闻学”项目的同班同学,这个夏天均在华府的各类媒体机构实习——有的在彭博社国家事务局(Bloomberg BNA)担任研究员,每天的工作就是一个上“山”下“山”的过程;有的在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担任实习记者,一次聊天时神采奕奕地跟我说起自己已经发表了超过三十篇报道的神奇效率,直到夏末的时候还无意中发现其中一篇报道已经被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网站转载;还有的前不久刚亲临了茶党(the Tea Party)在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门前对于奥巴马内阁“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俗称 Obamacare)的抗议行动,回来之后却悄悄告诉我:浩大的游行队伍里好多些都是他们招来的实习生呢。
我当然也并没有闲着。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旗下位于华盛顿的 WUSA-TV 电视台做了八周的多媒体实习记者,负责政治(选战)、科技、本地等领域的线上报道。
我待在新闻编辑室的这段时间里,见证了宾州州立大学师生因“桑达斯基性侵案”而痛失队史荣誉的扼腕痛心,亲历了席卷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哥伦比亚特区三省带来大面积停电的飓风灾后报道,更是“十足幸运”地参与了科罗拉多影院恶性枪击事件的后续庭审报道——请千万不要指责我的政治不正确: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能赶上五年一遇的特大枪击事件报道,实在是一个太过难能可贵的锻炼机会。
多媒体记者对于我来说已经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职位了,并且我一直笃信未来的出版行业都得逐渐向线上迁移。后来我在社交场合遇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 Suzy Kianpour,一周之前她还在墨西哥报道总统大选。在聊天过程中她说道:在墨西哥做报道的时候,出镜记者是她,视频编辑是她,采写报道也是她——“你还得会西班牙语,会发微博(tweet)。你必须精通所有事情。”
一方面,新闻行业的从业者们都像日复一日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us)那样从事着亘古不变的采写惯例(journalistic practices),另一方面,“讲故事”这样一门古老的手艺本身却因为社会信息的爆炸和冗余而开始带有着些许荒谬的色彩。我曾经在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华盛顿分部作为现场观众参与录制拥有全美最高收视率的晨间访谈节目 Meet the Press,事后节目主播大卫·格利高里(David Gregory)对着我们这样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记者们说道:“别指望在课堂里能学到太多东西,因为这个行业实在是变化得太快了。”作为一个已在新闻学课堂里孵化了三年新闻理想的科班学生,我竟完全同意这样的论断——几天之后我在距离 K 街不远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盛顿编辑部同该报的调查性记者 Brody Mullins 谈起他们 1997 年在业内大报间首创的“付费墙”(paywall)商业模式的时候,他曾向我透露:五年前当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对《华尔街日报》进行收购之后,有一批上了年纪的记者选择了离开。这其实并不是管理层的决定,而是由于那些早已谙熟纸媒发行规律的老前辈们自知在新闻娱乐化、商品化的新趋势中手艺不再,饭碗终将不保。
好莱坞金牌编剧艾伦·索金(Aaron Sorkin)曾在 HBO 热播的电视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中借由主人公 Will McAvoy 之口说出了那句“社会学家已经证实,现在这个国家正处于自内战以来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时期。”眼下一个令人沮丧的基本现状是,任何经由总统呼号的国家变革都将在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的基本局势下变得举步维艰。因此一个始终让人无法忽视的事实是,那些常年置身于商业运营及受众爱憎漩涡之中的主流媒体,每当在一些发起所谓全国大讨论的时刻,都得面临着非挑边(take position)不可的窘境。
在美国三大有线电视新闻网中,MSNBC 通常会被视为观点左倾,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则往往会被判为观点右倾。而以报道突发新闻事件见长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尽管被观众认为相对中立,但也因此付出了日均收视率多年低于前二者的深刻代价。
人们总是倾向于收看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新闻,尽管有些时候这些故事不尽真实——就在连年讨伐福克斯新闻频道存在报道偏见的公众声浪看似愈演愈烈之时,一项由民调机构 Public Policy Polling 在 2010 年做出的研究报告则把貌合的公众意见指向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迷思上去:福克斯新闻频道成为了唯一一家在报道公信力方面获得普遍正面评价的新闻机构,就像它自身的口号所宣示地那样——“公平公正(Fair & Balanced)”。

就在这种“过时信息一文不值”和“受众执导新闻创作”的双重思潮作用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长篇累牍逐渐演化为电容屏上的只字片语。当一篇报道的优劣已经可以通过定量的方式进行衡量的时候,收视率、点击量和时效性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考验着新闻编辑室里紧绷着的每一条神经。
事实证明,在显而易见的维度上对绩效所展现出的近乎狂热的渴求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肆意蔓延——当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对“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是否涉及违宪的问题进行终审宣判的时候,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现场记者仅凭内部线人的零星情报就在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冒险宣告“奥巴马医改”被高院终审驳回,闹出了一个持续发酵了好几个礼拜的乌龙笑话,也一时间成为了华府诸多媒体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我的一位当时在全国广播公司实习的同学就曾告诉过我这样一个细节:就在最高法院宣布判决结果的那会儿,他们的微博只比竞争对手晚了几秒发出,他的主管便直接在新闻编辑室里爆出了粗口。
然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口,恰好听闻一个曾在华盛顿结识的年轻记者在她所在的校园里发起的一场针对学校管理层的抗议行动。她是学校校报的主编,但由于学校最近指派了一名教职工来到报社以“监管”他们的工作,于是整个校报编辑部的学生便决定无限期罢工以示抗议。这样实际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突然让我开始反问自己:与其说这个行业本就如同大家所批判得那样与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如何脱节,是不是倒不如说我们记者做得还不够好、整个行业本身做得还不够好?
晚几秒,真的那么重要?
《新闻编辑室》中曾有这样的台词:“在一个民主国家,没有什么能比选民的知情权更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信息闭塞,或甚至是虚假消息,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决策,抹杀百家争鸣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从事新闻行业的原因。”每每读来,朴实的话语却总是莫名地给人坚持下去的勇气。
在乔治城大学的课堂上,新闻伦理学的教授曾经给我们分析过这样一个案例:在 2008 年 4 月 30 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一篇名为《美军在萨德尔城深入行动》(U.S. Role Deepens in Sadr City)的报道文章旁边,当值编辑用了非常大的版面刊发了一名伊拉克平民儿童炸伤后被抬出瓦砾的照片,照片的底下标注:“这个两岁的孩子后来死在了医院里。”
这个排版决定事后在新闻界曾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许多读者在乍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固然会不由自主地认可《华盛顿邮报》在战地报道中所传递出来的人性关怀,但同时我身边也会有同学立刻尖锐地指出:“这也可能是为反战而做的政治宣传(propaganda)。”我总觉得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一纸空文:相反,它能教会我冷静思考局面、弃绝人云亦云。
如果终有一天答录机停止工作、纸笔在包中积灰、快门停止闪动、网站不见更新,人们还是会想起记者,还是会渴望公正准确的事实真相。求取平衡(balance)从来都不应该是杜绝偏见(bias)和成见(stereotype)的借口,事实才是每个记者应该无限接近的目标。
作为一个年轻记者,越涉足新闻行业,我越觉得从事新闻报道就像是在手持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很多人嫌累可能早已弃之一边,很多人更有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手起剑落的那一瞬间。但一切正如加缪(Albert Camus)笔下那场“烈焰背后的苦涩(a bitterness beneath a flame)”,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从事新闻行业的原因。
(题图为作者本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