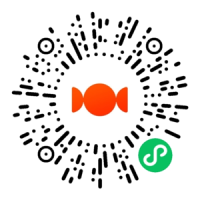为何曾经人人担忧的“网瘾”逐渐没人提及了?
先说一个真实故事: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的堂姐和一个游戏开发工程师相了一次亲。这个工程师和大家印象中的工程师差不多,长相低调穿着低调话也不多,并不是很讨姑娘喜欢的那种类型。不过从我跟他简短的对话来看,还算个靠谱的人。相亲完毕之后,堂姐家的长辈就开始议论起这个工程师的职业,对话基本上是这样展开的:
“听说这个男孩子是做游戏的。
那不得了,做什么不好做这种害人的事。
就是!说什么工程师,肯定是那种在网吧打游戏代练的,这种有网瘾的男孩子没前途的。
哎呀,那谁谁怎么给介绍这么个人…”
这可能是我眼见过最真切的“网瘾扰乱生活”案例了,只可惜,一个正儿八经的工程师被长辈们脑中扭曲的观点妖魔化为一个“网瘾青年”。
再硬造一个不好笑的笑话:有个难辨真假的段子是这么讲的,1979 年,瑞典还认为同性恋是 “一种病”。聪明的瑞典公民对此规定感到愤怒,奋起反击——他们纷纷请了病假,病假原因是 “我觉得今天我有点 gay”。
到了 2009 年,中国还认为网瘾是“一种病”。聪明的中国公民对此规定感到愤怒,奋起反击——他们纷纷请了病假,病假原因是 “我觉得今天我有点网瘾”,后来这些人都被送到杨永信那里去了。

如果同性恋不是病,那么网瘾同样也不是病
苹果 CEO 库克公开宣布出柜,好莱坞女星艾伦佩姬公开宣布出柜,得益于名人的推动和移动互联网让信息流动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知到,同性恋并不是疾病,是正常的。事实上,医学界认为同性恋不是病要早得多。
1973 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去除。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去除,认为同性性倾向乃人类性倾向的其中一种正常类别,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或不正常,且无需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疗。
2001 年,在 “中华精神科学会” 推出的第三版 “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如果说国际社会还一度真的曾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的话,那么“网瘾是病”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特色了。现在在中国特色搜索引擎百度中输入“网瘾”,还会出来一大批网瘾治疗机构。
“网瘾是病”这件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玩笑。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这个名词最初是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 · 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想拿《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IV)开涮,因为酗酒、赌博成瘾等 “行为障碍” 缺乏生理基础而编造出的概念。没想到一经提出,竟被很多网友对号入座,引来精神卫生界一场持久的争论。
2007 年,美国医药协会拒绝了对美国精神病协会将 IAD 纳入 DSM-V 的建议,批准对 “网络游戏滥用” 进行进一步研究。
后来戈登伯格已经声明该假设只是在一个社区论坛里当成玩笑提出的,是自己的恶搞。在 1997 年他曾对《纽约客》表示:”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
即使是全球最先提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美国心理学家金伯利 · 杨,也认为网瘾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而是已知的 “冲动控制障碍症” 在网络使用者身上的体现,也就是和电视病空调病等等一样,只是长期接触从而造成了心理上习惯性的依赖,可以归为心理问题但绝不能称之为一种病。
即便是在国外,也曾经一度出现过网瘾治疗所,2004 年,荷兰人凯特 · 巴克聘请了 20 多名具备专业资质及多年经验的瘾症治疗人员尝试按照精神疾病来诊疗网瘾。两年之后,这位荷兰人宣布他们对网瘾的治疗失败,因为网瘾并不是病。
就当我查阅到以上资料的时候,我又看到 2013 年一条被中文媒体转载多次的消息:
被视为精神医学领域 “圣经” 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做了近 20 年来第一次重大更新,在关于 “网络游戏成瘾章” 中,全盘采纳了我国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治疗室主任陶然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
这条消息一度让我感到茫然,于是我又去找了一下《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并没有找到什么 “网络游戏成瘾章”。事实是,”网络游戏成瘾” 被列为值得 “进一步研究” 的情况,并不属于精神疾病。
也就是说,“网瘾是病”这事儿完全是中国特色,涉及的链条很长。比如上面所说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治疗室主任陶然,就做了不少的百度推广,这些推广现在还在。
而不少民众反映,北京军区总医院曾经也有一些科室是外包的,比如非常赚钱的泌尿外科,整容科等等。至于这个一直宣传“网瘾是病,一定要治”的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治疗室还有一些诸如“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的马甲名称,主要业务还是治疗网瘾,月度收费达到上万元。
简单一查,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条非常类似于“莆田系医院和百度推广”的利益链条:某机构某些所谓的专家宣称“网瘾是病”并宣布制定了标准,标准被国外权威机构认可;不明真相或者明白真相但有利益关系的媒体夸大事实宣扬此事;更多的媒体争相转载;百度推广推波助澜;最后就是不少家长上当,交给这些没有医疗资质的“网瘾治疗机构”大量的费用。

(山东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为何曾经人人担忧的“网瘾”逐渐没人提及了?
人们开始理性对待“网瘾”是人们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这和人们开始理性认知同性恋不同,并不是要成为同性恋才能理解同性恋。但人们认知趋于理性有两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移动互联网进一步让信息流动去中心化了,并且这种去中心化让人们认清,在医学上,同性恋和网瘾都不是病。
前面说到,“莆田系医院和百度推广”的利益链条模式,这是建立在 PC 互联网上,搜索引擎是最主要的信息和流量入口上的。从这一年人们对百度的口诛笔伐,以及百度无力反驳只能认栽的情况来看,百度对互联网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了。
这几轮发酵于知乎、新媒体、微博和微信等渠道的起底百度运动可以说是常识和民众的胜利,人们冲散了曾经牢固的利益链条。
现在的情况是,以“网瘾”为关键词,在百度和知乎或者微博上得到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同时,人们的信任体系也变了。
我们正在脱离一个垂直信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信任那些看起来比自己权威的人),转向一个水平信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听取同类人的建议)。
一度我们以为“央视+专家”是权威,后来我们以为“百度+专家”是权威,现在我们开始更信任知乎和微博上大家的现身说法。这种信任体系的变化可能是好事,比如我们不再相信杨永信和陶然这些所谓的“网瘾治疗专家”;也可能是坏事,比如我们可能会沉浸在一种社交媒体回音室效应。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没人说网瘾,是因为大家都有网瘾,连爷爷奶奶辈都离不开智能手机了。
不过我更喜欢“数字分身”这种说法。
英剧《黒镜》中有根据社交网络语言和行为来再造一个人代替已故之人的情节,《Her》里面的人工智能和人相处越久就越善解人意,这都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故事。现实生活中,语音助手会分析语意和语境,互联网企业和广告公司正在分析网民的用户画像。
在 PC 互联网和端游时代,我们的“数字分身”比较像是“我们幻想要成为的人”,比如很多现实失意的人会在游戏中起一个狂拽炫酷的名字,某种程度上,我也认为 YY 直播上的喊麦主播说唱的那些“帝王、成仙、江山、美人”的歌词是这种网络文化的延伸,事实上,直播江湖中的工会,很多都是从端游里面的工会转战而来。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和人们的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游戏之外还有社交和工作。于是,我们的“数字分身”就更像“我们真实的状况”。
研究媒介和社会理论的哲学家鲍德里亚预见过这么一个人类未来:
“必须看到现代技术驱逐人类本身的现象。不管是通过具有驱除魔咒功能的言语还是通过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在这些赝象的境遇中,人类正在通过一种不可逆转的迁移和替代过程来消失自身。”
不过他所说的“技术赝象”更多的是指他那个时代的广播和电视,还没有谈到现在的电脑和智能手机,更不用说虚拟现实。而且鲍德里亚也预见到了,媒介现实将会“比现实更现实”,最终让现实消融。“数字分身”跟真实自己的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
正如每次我们看 IMAX 电影都会听到的前置广告词“看一部电影,还是走进一部电影”那样,技术一直在构建虚拟的现实,延伸的现实和超现实,我们半夜醒来第一件事抓起手机,看看微信有没有新消息,朋友圈有没有新回复,无非是我们现实社交在时间上的延伸。如果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发展到一定程度,光场技术以及全息影像技术门槛更低,虚虚实实就更难分清。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正在营造一个会让我们越来越让人沉迷的现实。而“网瘾”这回事,对于接触这些技术的人们来说,也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