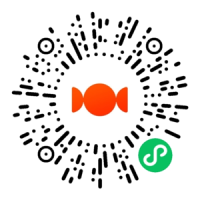百年渡口,十日网红 | 浮世
本文转自博物志(微信号:szszbf),原标题《百年渡口,十日网红 | 浮世》,转载时已获得作者允许。
水面持续上涨
把李国新的命运围成一座孤岛
这辈子再没下渡船
文 | 王笑笑
编辑 | 小肥人
摄影 | 王笑笑 吴欣怡
采访 | 王笑笑 吴欣怡 小肥人
「你说他们记者炒作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聊天当间,李国新突然又丢出这样一句话,像块石头「当啷」一声掉在跟前的玻璃茶几上。几十分钟前他刚送走上一波记者,茶几上刚沏的茶水还温热冒气。
「也包括你们,宣传的目的我都不明确,都给我弄糊涂了。」
李国新是个艄公,在距首都市区三十多公里的地方摆渡着一条舢板。数十年的生活像绕着河面旋转不辍的陀螺,只有凑近才能看到历史在上边留下的细微划痕,直至另一个世界的一件小事让它和一只更大的陀螺发生碰撞,又倏然弹开。
而就在碰撞发生的那个瞬间,李国新和搭档被甩到陀螺的边缘,以普通村夫的身份出现在刺眼的聚光灯下。这种体验令其倍感不适,也无法理解个中缘由及逻辑。
一、潮白河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自言自语给出了回答,「两会,肯定出了事儿了!上访的,没拦住。」此时是两只陀螺发生撞击的那一刻,扰乱了他所习惯的那种旋转。对于这样不合常理的冲撞,李国新要在自己熟知的世界观框架里寻找解答。
前一阵子进京安保严格的时候,渡口每天有五六个干警协警守着,盘查往来路人车辆。李国新想了会儿,自己就是一摆船的,「没义务也没能力判断船上的人是不是坏蛋。」就算出了事情,他也没责任,于是便松了口气。
生活的平静是被一封贴子打破的。两会期间,燕郊进京大堵车,有出租车司机绕路到这里摆渡过河,再上高速进城。事主将此事发到论坛上,此前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小渡口迅速蹿红。
李国新在午觉中被我的敲门声吵醒,这几天他因坐骨神经痛休病在家,由搭档暂时顶替。他伸了个懒腰,从衣架上取下迷彩外套披在身上。儿子一家三口和尚未结婚的女儿都和老两口住在一起,一台老式座钟靠在墙角「滴答」作响。
他不住打着哈欠。聊到最近来拜访的记者,他从茶几下掏出来一厚沓名片,放在手里看了看,撇在几面上,「总共这一堆呢。」几十张名片分别从北京、廊坊和石家庄来到这儿。「也记不清哪是哪的,忒乱,忒乱了。」
「李连老师傅啊,都被你们采访得进医院挂水了!」一个村子大多沾亲带故,从辈分来看,和李国新搭伙摆渡的李连是他的舅舅。
北京的疆域向东延伸到这里,撞上这条几十米宽的小河,便就此止步。于是潮白河就成了北京和河北的界河,西边是北京市通州区的尹家河村,东侧是河北省香河县的王店子村。一河之隔,在北京最边缘的农村里,村民们的养老金比对岸河北高两倍,两村高考录取分数更判若云泥。早些年,河东岸的人家都想把姑娘嫁到对岸去。
站在河西,耳边顺风吹来对岸闲聊的只言片语。然而在导航里,到对面要驾车行驶十五公里,路线沿河伸展,在密布的水网中三次跨河,再转头回来一路向北。

(图一:地图上过河建议路线)
李连说不清最早是谁开始在这里撑船摆渡,他十四岁起跟随父亲在此渡人,今年已七十有余。除去中间当兵和做矿工的几年,他大半辈子都在河面上度过。
舢板由铁皮焊成,再用木头拼成船面,足有近二十平方米大,够停得下一辆小轿车。舢板用滑索链到跨河的钢缆上,防止被冲到下游。这样的跨河索道,艄公们一共布置了四条,从北而南依次增高,若是涨水则解开舢板、换成向下的另一条。
过河费多年未曾变过,行人一元、自行车或电动车两元,要是有开车往来的,花上十块钱就连人带车一起给你渡过去,免了十几公里的冤枉路。
舢板靠岸,李连下来拉起船头的铁链,扬手一甩,铁链在岸边的木桩上绕了几绕。再哈腰,抬起河边的木板一左一右搭在船沿,汽车两个前轮便正好轧在板上,一脚油门即可上船。几位行人跟上后,老师傅解开铁链,捡起船上的木块塞到车轮下。
这天风很大,舢板斜在水中,河水在船边激起层层浪花。李连站在船头手抓索道,身子使劲向后仰把船往回拉。「李大哥上哪旅游去了这两天?」一位坐船的女子一边帮忙拽着索道一边戏笑道。
前几日因晚上在河边受访,遭了风寒的李连眼皮没抬,没好气地嘟囔,「还旅游,差点去火葬场旅游!」

(图二:附近村落及渡口位置)
二、外来闯入者
渡口在王店子村这头修了个水泥房,作为艄公摆渡间隙歇脚的地方,也常有村民过来下棋。我第一次见到李国新,正是一天中往来渡河最少的时候。他坐在水泥房门口的破旧沙发上,头顶正上方的墙面修了「百年渡口」四个篆体字。一身迷彩的老李脚边放着大号保温瓶,一手端个瓶盖准备喝水,另一手配合话语比划着。
此时他是人群的焦点,身旁站着某家媒体的两个摄影记者,眼下正对他软磨硬泡,哄他接受采访。这样的场景每天都有,前一波记者没来得及走便和后一波撞在了一起。作为回应,李国新翻来覆去重复着,「我不信你们,你们记者不可信。我就信画出来的画,照片和文章都不可信。」他嘴上对两个记者说着,眼睛从人群中的每张脸上一一扫过。
我身处于人群中,没一会儿也成了话题之一。来往几回合,一位老先生问道,「哪个大学毕业的呀?」我小声报了学校名号后,老先生迅速从舌齿间丢出仨字,「拉倒吧」。这种反应令我始料未及。
「你能考上 XX(某 985) 大学?」他半伏在三轮车车厢上,乜斜倦眼,连问三遍。
我辩驳了几句,老先生却越说越气,后来竟拍着三轮车栏训斥起来。「你要说你是廊坊 X 学院的,我信,XX 大学,我不信。」我稍微有些明白了—— X 大毕业生应该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指点国家大事,而非现在在村口和他们扯闲篇。
李国新在旁津津有味地看着。相熟的村民在摆渡时和老李戏说他都成网红了,李国新自嘲,「还网红?我都快紫了!当网红有什么好?」和许多村民一样,他始终不理解这有哪里值得采访。对于他们,渡口不过是漫长岁月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
有位记者上船帮老李一起摆渡,过河的一位年轻人瞥了眼他,一边手上帮忙牵引索道,又一边自顾自地和艄公说道「这帮记者啊,就炒作有能耐」,话语像刀锋般从那位记者面前划过,「让他去政府那要钱,你看他们敢不敢?」每个字都暗藏指向第三者的锋芒。李国新在喉咙里咕哝了声表示赞同。

(图三:应付记者的李国新)
「也不知道谁一开始在网上说的偷渡,是我让他们来的吗?我在这就为了这几个村子来回方便,谁让他们从燕郊跑这来的?」那封燕郊的帖子走红后,有朋友告诉老李,网上传开的题目是「燕郊居民偷渡进京」,他知道后气得够呛。
「只有越国境的才叫偷渡,不存在偷渡,从这儿走怎么叫偷渡?你说是不是荒唐?他有没有文化?无知!」这口气一直悬在胸口消不下去,让老李隔几分钟就拎出来抱怨一番。
前几天他在气头上,有记者来拍照,被李国新制止。记者辩驳说这地又不是你的,二人便起了争执。火上浇油,最后他把那记者生生骂跑了。回来后火气稍减,老李又自觉这么干不太厚道。
渡口走红后,水泥房里又进来了不少政府工作人员。有人自称是廊坊海事局,叫老李加强渡口的安全措施,李国新回应道,「你他妈还廊坊海事局,我没听说过。」对方称部门新成立,老李心中暗骂,「你新成立的,我这一百多年了,你来领导我?我领导谁去啊?」
水路不同于陆路,一旦出事,车进水会彻底报废,甚至人也会有生命危险。李国新虽懂小心驶得万年船,可渡口也并非没出过事。
2009 年春节,正是来往最繁忙的时候,某天满满一船的人和车带着年货过河,未及靠岸,一辆三轮车误挂倒挡,将后边另一辆三轮车撞下水去,水果罐头飘了一河面。落水的三轮车彻底报废,车主起诉李国新。法院认定摆渡属于营运行为,建议老李出钱私了。李国新不同意,并不是差这几千块,而是一旦低头,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船不安全,他不能接受。
他至今不忿,认定这事绝不是自己的过错,他用下棋作喻,「你们两个人下棋,一个把另一个下赢了,和我这棋盘没关系。」事情并没有意外的结局,考虑到肇事车主家中实是贫困,李国新最后也没说啥,卖了头牛,赔了钱。
院子里养了只漂亮的金毛犬看家护院,此刻正对着外来者汪汪叫。
三、摆渡人

(图四:渡口旁的文化墙)
天气好时向北眺望,能见到一公里外的水面上有另一条舢板,那是赵庄渡口。这段潮白河上的渡口原本有三个,其中一个因水坝修建而废弃,便仅剩现在这两个。赵庄渡口的船比尹家河渡口的更大,也更稳。但后者因地处两岸交通咽喉之处,因此要热闹得多。
赵庄渡口也是子承父业,本来是兄弟二人轮班,后来哥哥要接送孙子上幼儿园,留下赵作喜一人全天摆渡。同下游记者蜂拥的尹家河相比,竟无镜头对准仅一公里外相差无几的赵庄。前些年潮白河上采砂业盛行,留下一堆早就锈迹斑斑的钢铁怪物矗立在岸边,斜斜插入水中,守望着不远处每日相伴的船长。
临近村庄有许多养羊户,每日如钟摆般往返于村庄和集市,驱动赵师傅踩着分针在两岸穿梭。每天中午,他掐准时间渡完几辆小卡车,十二点准时拴船回家吃饭。这天他正准备拴船,对面却突然尘土飞扬地开来一辆吉普,「修高速的。」他摇摇头又过去接他们。正在修建的环北京高速从空中穿过,刺破了摆渡人单调的生活。
尽管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他从未去过尹家河渡口,船客嘴角漏出来的一言半语全灌进他的耳朵,成了有关下游消息的唯一来源。秋来春往,河面上仅有的同行之间竟几乎不曾谋面。
赵作喜年幼时就听过要修桥的传言,便想着先接过船篙当作暂时的营生。没想到这桥直至今天也没个影,摆渡在日复一日的企盼中,竟成了一生的事业。数百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横跨潮白两岸,渡口是一天都不能停的。要是没人接手这条船,他就只能独自迎接西西弗斯式无法逃离的宿命。
1983 年,火车载着三年军龄的李国新回到家乡。服役时,他在炮兵指挥连计算炮位和炮轨,这在当时是高中毕业生才能进的兵种。
「就在地图上,拿小针一扎」,李国新从沙发上站起来,眯上一只眼睛,捏起拇指和中指,「用仪器算完后告诉炮阵地,用加农炮、火箭炮,用多少标尺打多少距离,特别准!」说起在部队的故事,老李午后的困倦一扫而空。
河北农村户口的复员兵不管分配,他一直想着,要是生在河那头,当初找找人说不定能在地方上给条出路。在部队,他还是全连合唱的指挥呢!但在那个年代,一个退伍兵能做什么音乐相关的工作呢?他又摇摇头。
当年回乡时正赶上土地承包改革,分了地后,他又干了一年瓦工。农村那些活计,八成以上老李都会干,若是做瓦工,一天能挣两百多块,相比于现在风吹日晒挣一天百八十块,可划算多了。可从军队里回来的人觉着再做什么都没意思,于是渐渐也少了再活络的心思。
李国新兄弟三人,他是老二。父亲年纪渐长,渡口的活计需要有人接班,哥哥不乐意干,弟弟脾气不好,渡船时三天两头和人打架,李国新只得登上舢板。早些年的潮白河水量比现在少很多,经常五天来水,三天干涸,老李就可以趁着干涸继续干他的瓦工活。后来水面持续上涨,把李国新的命运围成一座孤岛,他这辈子再没下过渡船。
如今年过花甲,李国新自认家庭美满,更多将摆渡视作不求回报的「为人民服务」,更无尝试其他营生的想法。「也没人愿意要,谁要你这老头啊。」他喃喃说道。
只在话头缝隙间,他会不经意提到当年一起当兵的同乡里,现在有几个已到师长级别。
四、另一块砖
打眼望去,王店子村的民房是一溜的白墙红瓦,朱红色的大门上嵌着仿制的鎏金铜钉,有丝像过去的相门王府,颇具气派。在去年的新农村改造中,承建的华夏集团一同还在河边立了面大白墙,上书「百年渡口」四个大字。
「百年渡口」是它被正式提及时的名字,而渡口的历史很可能比村民记忆中长远得多。几年前,曾有附近小学的老教师走访周边村子老人,撰写渡口回忆录。如今说得清历史的老人们大多作古,老教师也在回忆录完成前就卧病在床,将这份回忆录交给西集镇史志办整理。
从他整理的历史来看,自建村以来,就有渡口存在,距今已五百年有余。两百多年前,村里曾有位大财主投资修建了一座八孔石桥,又不知在何年月被大水冲垮。李连说石桥没有垮,只不过被抬高的河床埋在了淤泥下,他回身指向旁边的一片空地,「就在那,有年发水冲出来块石头,我还在上边停船。」
说到建桥,附近的村民们认定是两个政府之间的推诿扯皮才拖搁此事。没有桥,两个村子分别处在北京和河北交通的死角,他们认为这「桥」和附近经济的落后不无关联。
建国后,渡口由大队接管,尹家河和王店子各派两人在这里为来往村民摆渡方便,和其他农活一样计工分。改革开放后,一切照旧,只是工分变成了金钱,从一开始的五分钱一次,逐渐涨到现在的一块钱一次。
2012 年 7 月,北京大暴雨,冲坏了之前的舢板。在打造新船之前,渡口停了几天,此外数十年来渡口不曾停摆过一天。摆渡用的船加上几条跨河的钢缆造价要三万多块,全由李连和李国新二人平摊。让人不解的是,两村居民、亲朋好友、国家干部、红白喜事,往来过河不收费的竟占了七八成以上。若赶上天气不好,老李最惨的时候是在河边守了一上午只挣了八块钱,可要是赶上过年前后的高峰期,两岸过河要排队,需四个人一起摆船。
摆船不仅是个体力活,来往行人的行动坐卧、身伴手提,艄公的眼睛里要能装进东西,脑子还得记住事儿,须看出人家的去处和去意,若赶上赴红白宴,这一两块的过河费是万万收不得的,个中规矩大得很。这不仅是出于对乡土社会中人情规则的遵守,更是对古老传统的尊崇与忠贞。
「传统」二字在李国新的口中被多次重复,渡口原本是两个村子各出二人搭伙摆渡,自己村民不收费。后来对岸逐渐退出,只剩王店子独自出人,摆渡依然对尹家河村民免费。对于此事老李略有不平,但旋即又释怀——大家都认识,也有人经常给他扔盒烟或扔点蔬菜瓜果。一天多不出二三十块,突然要钱就不合适了。
李连只有一个女儿,李国新一儿一女,儿子不乐意干,女儿在廊坊家具城做买卖。两位艄公对渡口后继无人的现状,心里也没底。有附近的村民讪讪地说,渡口是挣钱的好门路,艄公们不会让外人接手这份工作,待他们老了,也会在家里挑男丁塞上去。
李国新却始终将自己的行为视作「挣点良心债」,子女总劝他不要再做这件事,他一拍桌子,「我就是要当这个雷锋!谁能拦得住我?」但他自知河上的工作的确很辛苦,「冬天冷着呢!那夏天,热着呢!」在李连口中,夏天蚊子多的时候眨巴眼睛都能夹死一只。假若真有后继者,未必不可尝试给摆渡涨价,这是李国新想出的唯一办法。
提价的事情,李师傅不是没想过,作为附近村民出行唯一通道,地处往来交通要地,虽不至漫天要价,但提至与劳动匹配的价格还是合理的。可涨与不涨、收费与不收费,他将其视作一个道德层面的决定。对大部分人不收费的传统习俗,老李无法打破。
连年的付出都存进老李在人际中的「人情银行」里,他成了村子的头面人物,两个村子但凡摆桌设宴,几乎没有不叫上他的。李国新也有个念想,希望党和政府能照顾照顾,每个月适当给些补贴。

(图五:正在摆渡汽车的李国新)
「虽说不是真正的雷锋吧,但我也算一半的雷锋了。我不求这个,但政府应该有这样的良心。」他坐在沙发上,右手夹着云烟,口中吐着烟圈徐徐说道。他拿着我们的书看了许久,「另一块砖,这名字起得不错。虽然词汇不怎么样,但意义在这。」
「你觉着是个什么意思?」
老李想了一会儿,「说不出来」,他顿了顿,「甘当另一块砖吧。」
五、尾声
聚光灯落下了。
李国新的「网红」当了没几天,猎奇的外来者便迅速减少。十几天后,来访记者便已寥寥无几。用网络原住民们熟悉的语言说,他是「过气」了。
陀螺只摆了摆,没多久便恢复了旋转节奏。
影响并非没有,渡口获得关注后,有私人企业找到这里,希望能出资建桥。村里有声音,觉得不希望破坏「文化遗产」,李国新对此反倒不抵触,渡口保留百年本就是意外,而被现代信息机器冲撞过的那块舢板,远不是一条钢索可以把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