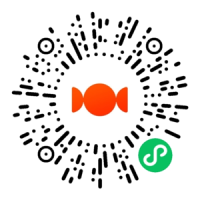他是《硅谷》中的 Dinesh,他在真实的硅谷也有很多故事
这是 ONES Piece 翻译计划的第 129 篇译文。本文原载于 newyorker.com,作者 Andrew Marantz 由 ONES Piece 杨绍华、Pan 翻译。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新、生活方式和未来商业。如果您希望得到更「湿」的信息,我们也有播客节目「迟早更新」供您收听。
2009 年,在大卫·莱特曼晚间秀上,喜剧演员库梅尔·南贾尼身着黑色西服,戴着无线麦克,走到舞台上,表演他的单口喜剧。乐队演奏了《出生在美国》的几个小节,大概是暗指他不是出生在美国这个事实。南贾尼第一个段子没效果不佳。他僵硬地站着,用力地吞咽,双手紧握在胸前。然后他讲了另一个笑话,关于那些背景故事过度复杂的主题公园设施。
他说:
这就像色情电影的剧情。
我真的不在乎里面的主人公是什么职业。我就是来玩儿的。
在南贾尼的表演中,这个梗不是最妙的,却引发了大笑和长达 10 秒的掌声。他大口地呼气,放松了双手。他的下一个段子是关于旋风过山车的,就是康尼岛上那个摇摇晃晃的过山车。
旋风是在 1927 年制造的!你好好想想。他们应该把名字改成 1927,因为这个事实比任何一种旋风都可怕。
而且这整个儿过山车都是木制的……你知道,就是 NASA 用来制造航天飞机的坚不可摧的材料。
这个段子可能已经在 1960 年代时被伍迪·艾伦或者莫特·萨尔(Mort Sahl)用过了,不过有一个例外:南贾尼说那次过山车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而我还是在巴基斯坦长大的呢。”
南贾尼在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度过童年。1997 年,他离开家来到爱荷华州中部一所叫做格林内尔学院的小型文理学院。“从看电视等事情上,我想,美国各处像是一个地方”,他告诉我,他们只会向你展示拉斯维加斯、纽约这些城市,不会告诉你有关爱荷华州的事情。
上大学时,他说:“我很害羞,但是了解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很有趣。”大四时,校园里有一个公用麦克风,他的朋友们鼓励他试试单口喜剧。他表演了 35 分钟。
我想就观众反应来说,我之后从未做得比那次更好。当然,都是些认识我的人。但那让我自信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毕业后,他搬去芝加哥,开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迈克尔·修华特,一名喜剧演员兼导演,从开始就很欣赏南贾尼。他告诉我,任何一个见到他的人都能看出来他很聪明,声音很独特。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会成功,而是他选择进入哪个方向。
在登上大卫·莱特曼晚间秀的同年,南贾尼得到了电视节目《科尔伯特报告》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角色,饰演一名住在斯蒂芬·科尔伯特桌子下面的关塔那摩被拘留者。南贾尼最早期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有很多,“或多或少是你能想到的”:快递员、修电视的、巴基斯坦厨师。但很快他就开始出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几年,他已经出现在了几乎每一档热播节目中,包括《波特兰迪亚》、《大城小妞》、《废柴联盟》,《基和皮尔》和《艾米·舒默的内心世界》。

目前他在 HBO 电视剧《硅谷》中担当主角,扮演一名相貌英俊却没什么桃花运的程序员。
这就是高中时期的我,那是我最不自信的时候。
孩提时代,南贾尼在家说乌尔都语,在学校学习英语,并从电视上学习英语口语。“我看着《捉鬼敢死队》、《霹雳游侠》、风火轮广告长大”,他说,“在上大学之前,我还从未去过美国,但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却比我的朋友们都多。”
作为一名单口喜剧演员,他说:
我特别渴望不是以移民喜剧演员的身份被大家认识,或者是穆斯林喜剧演员;那样的话,我只能穿个T恤,说说视频游戏。我并不是批判其他喜剧演员利用他们的背景优势——加入香辣咖喱喜剧之旅,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我自己可能从来不会这么做,尽管我本可以这样做。
然后 9·11 事件来了。“突然间,伊斯兰教成为众矢之的。”南贾尼继续说,“好吧,我只是想,我是有色人种,我说话有口音——至少我必须提出来。”他开始说:“别担心,我是那群好人中的一个。”这让一些观众安心了。其他时候,他会被一些大喊“回家吧!”或者“滚回塔利班”的人打断。
回想起在密尔沃基的一个俱乐部,有一个质问者,南贾尼说:“房间很安静,很尴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试图忽略他。观众很同情我,但这对于喜剧表演来说并不是好事。之后,我想出来该说些什么了——我意识到不一定要是一句完美的台词,只要说些什么让观众明白一切还在你的掌控之中。”下一次他被质问时,他回应道:
那家伙是对的。我是个恐怖分子。我只是暗地里表演单口喜剧,保持低调。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南贾尼的电影《大病》(The Big Sick)中,只不过“塔利班”变成了“ISIS”。今年早些时候,该片在圣丹尼斯电影节首映,并成了观众和影评家的最爱。电影由修华特导演,贾德·阿帕图制片。修华特在其导演生涯中拍摄过邪典闹剧经典(《哈拉夏令营》)和另类浪漫喜剧(《你好,我叫多雷丝》);贾德·阿帕图最近则专注于帮助几近成名的喜剧演员将他们的经历融入回忆性质的喜剧。

(《大病(The Big Sick)》海报,图片来自 comingsoon)
阿帕图的制片伙伴巴里·门德尔把《大病》描述为:一部分是关于喜剧的喜剧,一部分是关于家庭的戏剧,一部分是医学之谜,一部分凑巧是美国穆斯林爱情喜剧。
南贾尼与妻子艾米丽·V·戈登合作撰写了剧本, 并亲自出任主角,饰演一位名叫库梅尔的单口喜剧演员。这是他们已经写好的两个故事中的一个,也是南贾尼的第一个主演角色。虚构的库梅尔是一名 Uber 司机,当真正的库梅尔还在上班的时候这种工作还不存在。除了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帮助抖包袱或者使剧情连贯的设定,这部电影和戈登、南贾尼两人在十年前即将步入三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很大不同。
南贾尼毫不认为这部电影是关于政治的。“这应该只是一部温馨的电影。如果我们做好了,它会很有趣,可能还会有一点尖锐。”他说。但这是从去年夏天开始拍摄的,当时很多谈话不可避免会涉及总统竞选。此外,该片于 1 月 20 日在圣丹斯首映,而唐纳德·特朗普也在当天宣誓就职。
南贾尼告诉我:
这巧合实在怪异、可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感激我们新当选的总统是反穆斯林的,所以现在我和我的父母总算在政治上达成了一致观点。
阿帕图说:“我们从来没谈过‘在大荧幕上呈现一名世俗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我们谈过讲述库梅尔的故事,很自然这会把我们引到关于家庭、文化和宗教的问题上。”
这部电影将于 6 月上映,而它恰好出现在当前这种许多个人行动似乎充满政治意味的时刻:足球运动员在国歌奏响时下跪,或者乘客从飞机上被拖拽下来。这些事件都可能被电视专家与玩推特的政客变成一场国家的罗尔沙赫氏测验。
“我仍然不会把它看成是一部政治电影。但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猜现在一切都是政治。”
南贾尼告诉我,比如那个起哄的场景,写剧本的时候,设定很明确,人群中的这家伙就是个混蛋、局外人,而且观众也应该会自动站在我这边。
但现在与那个家伙如出一辙的一群混蛋已经接管了国家,我不确定这会有多么好笑。
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南贾尼是围绕着他认为能引起美国观众共鸣的主题来进行创作。当时路易·C·K 和其他喜剧演员们以一种涉猎广泛的忏悔式风格大获成功,他却坚持讲些有关经典恐怖电影、记忆的本质、单词“章鱼”(octopus)复数的简短评论性笑话。
他性格内向、害怕表演,但把自己的恐惧融入化为一个深思的舞台形象。皮特·霍尔姆斯也是一名喜剧演员,与南贾尼同期入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评论南贾尼:
他穿宽松的连帽衫,说话含糊不清。他真的很棒,就是有些诡异、絮叨、敏感——所以你得注意点。

南贾尼避免在舞台上提及的是他被培养成为一名严格的什叶派穆斯林。他被教导认为,好色的眼神或者喝一口酒会导致永久的折磨,并且古兰经是上帝准确无误的语言;因为古兰经没有提到恐龙,所以恐龙从来就不存在。
八岁的时候,母亲给他留了一件首饰,计划在婚礼上给他未来的妻子。无需赘言,南贾尼的父母会挑选这位未来的妻子,而她也会是一名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可能是一个朋友或者表亲。南贾尼离家上大学时,母亲让他答应永远不会屈服于西方的世俗主义。几天后,在格林内尔入学的一周时间内,他第一次握了女人的手。
但怎样才能让街头酒吧里某个喝醉的顾客觉得这段成长经历非常有趣呢?短短十分钟内,有太多术语需要定义,太多文化背景需要建立。此外,一个成功的笑话需要一个清晰的观点,但他的观点相互矛盾并在不断变化。
他将卡拉奇与诗歌和建筑、暴力和厌女症、美味佳肴、让人不安的肮脏、他爱过的每一个亲戚联系在一起。他的自我中有一部分认为将很快搬回巴基斯坦,而另一部分又知道他永远不会。他不能把这些想法完整、清楚地表达给自己,更不用说陌生人了。
到 2006 年,南贾尼表演单口喜剧已有五年。他和一个朋友住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平时是一名 IT 专员。“我明白,这是对南亚人来说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他说,“另一方面,我却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糟糕而感到自豪。”
他每周在城镇和路边表演三四个晚上。在这种时候,许多喜剧演员可能已经搬到纽约或者洛杉矶,在那里他们可以试镜得到电视台工作,并且可以被经纪人注意到。南贾尼则出于舒适和习惯留在了芝加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他训练自己把麦克风拿出来,并开始在舞台上走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小事,但它是革命性的。”他说。他把发型从 20 世纪 90 年代休·格兰特那样懒散的中分式变成了猫王的后梳式。“他开始变得强壮,穿紧身T恤。”福尔摩斯说,“他修了他那一字眉,提高了音量,开始控制全场,充满激情。这就像看到一辆汽车突然换到更高的档位。我开始喊他‘新梅尔’ 而不是‘库梅尔’。”

在 North Side 一家酒吧的某场表演中,南贾尼开玩笑问,“卡拉奇在房间里没?”观众中有个人也开玩笑地“嘘!”了一声。南贾尼看到她是一名白人女性,一名褐色头发里夹杂着一缕紫色的美女。“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会注意到你。”两天之后,他们再次相遇。她介绍说自己叫艾米丽·戈登,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身为一名情侣和家庭心理咨询师,她对于喜剧也知之甚多,还有电子游戏、漫画书、恐怖电影,和南贾尼简直如出一辙。
很快他们几乎每天都发短信。尽管互相吸引,但他们都对情侣关系却都不感兴趣:27 岁的戈登结过婚并已经离婚;28 岁的南贾尼不应该和任何一个人约会,更不用说一个非穆斯林了。“我们约会、做爱,又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了。但让我们再约会一次。”南贾尼说,“又一次,在她来看电影之前,我在床上扔了一堆脏衣服,以确保不会再发生什么事。结果还是没用。”
同时,南贾尼的父母已经从卡拉奇搬到了新泽西,开始给他发芝加哥地区他们认为合格的什叶派单身女性的信息。南贾尼则极力回避这些相亲。“我的美国朋友会说:兄弟,告诉你父母你不感兴趣不就行了。”他说,“但这是一种文化误解。在巴基斯坦文化中,包办婚姻才是婚姻。其他任何事情都是绝不可能的。”
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美国化,想要选择自己的爱情伴侣,但巴基斯坦血统又让他害怕辜负家人的期望。他说:
我无法想象一个我最终接受了包办婚姻的世界,但我也无法想象告诉我父母。我只是岔开话题、拖延。
在两人约会几个月后的一天,戈登给南贾尼发短信说要去看医生。之后南贾尼几个小时都没有收到她的消息。大约到了午夜,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戈登在急诊室,呼吸困难。他匆忙跑到医院,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由于处于深度镇静状态,戈登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变换。她的肺感染了,而且扩散很快。
医生告诉南贾尼,为了治疗,他们需要让戈登处于医疗昏迷状态,问他是不是病人的丈夫。他说不是,甚至连自己是否是她男友都不确定。医生又问,并催促他签了一份免责表单。最终,在医生的坚持下,他签了字。医生把戈登捆好,注射了麻醉剂。她挣扎了下,然后陷入了昏迷。
南贾尼本来应该在去见扎克·加利凡纳基斯的路上,但是他留在了芝加哥,并每天都去 I.C.U 看望戈登。她持续昏迷了一个多星期。同时医生排除了几种可能性,包括 H.I.V 和白血病。即使是十年后,哪怕已经讲过数十次,南贾尼无论在什么时候谈到这段经历,都会哽咽。“我就坐在她床边,”他回忆,“她没有意识,身上连着那些嘟嘟叫着的机器。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想,如果她能从这走出来,我就和她结婚。”
他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套,如果你仔细想想,甚至有些诡异、一厢情愿的。但那就是我的想法。”
“剧透预警——我活下来了。”去年五月,戈登说,向我竖起拇指并露出一个傻傻的微笑。在昏迷的第八天,她被诊断为成年型斯蒂尔疾病,一种罕见的炎症综合征。不过一旦被确诊,经过治疗,病情还是可控的。“我必须有适量的睡眠和锻炼。偶尔还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不得不卧床休息几天。”她告诉我:“但再没有什么 I.C.U,真他妈太好了。现在只有在拍电影时,我才不得不去医院。”
作为《大病》的联合编剧,去年春天,戈登每天都在纽约的片场拍摄。她和南贾尼现在在洛杉矶有一套房子,但在拍摄期间,他们住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一间 Airbnb。我第一次见到戈登的时候,她正坐在一把帆布导演椅上,守在视频监视器前,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旁边分别是制片人门德尔和导演修华特。
我们在威廉斯堡的一个艺术空间里。经过装饰的空间看起来就像小说里库梅尔在芝加哥的单身公寓:一台 Xbox、一个充气床垫、一个家庭装的麦片盒子。拍摄期间,扮演电影中的艾米丽的佐伊·卡赞就坐在真正的艾米丽旁边,聊各自正在看的书。那一刻,卡赞转身过来对我说:“你知道那种一年级生有这么个酷酷的三年级表姐,而且认为她棒极了的事儿?那差不多就是我对她的感觉。”
卡赞在空中晃着脚,眯起眼睛看着服装设计师已经挑好的一双灰色芭蕾平底鞋。“你真的会穿这鞋么?”她问戈登。戈登没有说话,做手势指指自己的脚:一双灰色的芭蕾平底鞋。
“很好。”卡赞说。
当工作人员准备就绪,修华特让大家安静,坐在监视器前戴上耳机。卡赞走进隔壁房间,她和南贾尼开始拍摄下一个场景:这对夫妻的第一次争吵。在电影中的这一刻,他们的关系进展不错,但库梅尔一直在回避一些传统的承诺桥段,比如把艾米丽介绍给他的父母。
电影中,艾米丽在库梅尔的房间翻找,找到了一个全是照片的雪茄盒——都是南贾尼的母亲试图介绍给他的巴基斯坦单身女性。艾米丽开始发问,比如“你能想象我们最终在一起的世界么?”这幕场景的高潮在于库梅尔的反应不足。
戈登告诉我:“找到一个真的装着照片的盒子,这是通过电影许可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布景明显来源于现实。这场冲突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冲突方式非常相似,相似到某种程度上让我有点看不下去。他回应冲突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去睡觉。当然这让我非常愤怒。”

(南贾尼和艾米丽)
当我摘下耳机的时候,能听到卡赞的声音从墙那边传过来,而在大多数场景里,都听不清南贾尼的声音;在监视屏里,卡赞边踱步边挥舞着手说话,而南贾尼则疲惫地靠着门柱,眼睛好似一潭幽深的湖水。南贾尼在《硅谷》和其他一些剧里的喜剧表演,展示了荧幕上所需的吸引力和真实感;而在《大病》这部电影里,充满着长时间的间歇和间断插入的轻松场景,他表现出了对紧张场景的把控力。
争吵的片段他们拍摄了好几遍,并对剧本里的对话做了即兴改变。每次开拍前,修华特都会敦促南贾尼把握好坦率与残忍的界线,把话说得更直接。在一个场景快结束的时候,南贾尼以接近耳语的声音说:“艾米丽,我们交往不过5个月,我觉得你反应过度了。”
“刻薄点!”孟德尔在监视屏边上说到。
“去你的,库梅尔!”戈登说,“我是指电影里的库梅尔。”
因为拍摄在快中午时开始快深夜时结束,他们的午餐时间在下午5点。南贾尼、戈登和卡赞决定走去附近的亚洲素食餐厅吃午餐。在路上,他们看到一辆拖车,是道具部门在准备接下来的晚餐场景。他们从皇后区的一间巴基斯坦烤肉店订购了些食物,正在确定哪些食物在镜头下最好看。南贾尼尝了些印度香米和 haleem,一种浓稠的小麦炖肉。“这些玩意儿是真的,”库梅尔说,“或许你们可以再弄些 barfi 来,那是一种有牛奶和糖的甜点。”
“Barfi 是吗?”一名制片设计问到,一边记下这个名字。
“Barf”,后面还有个“i”。库梅尔补充到。
他们继续走向素食餐厅。卡赞说:“道具部门的人很擅长这些,摆在我公寓里的书也很合适。”
南贾尼点头说道:“在有我的一些场景里,总会有猴子、大象、佛像和阿拉伯语字母——这些都是出现棕色人种时可能伴随出现的东西。”
下一个计划拍摄的场景是电影开场不久后的一幕,一场床戏。午餐结束后,卡赞和南贾尼模仿芝加哥的冬天穿上了厚毛衣,毛衣会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脱掉。卡赞说:“我觉得你的胡茬很棒,但肯定会刮伤我的脸。”
在前一晚的讨论中,库梅尔和两个艾米丽决定在拍摄这一场戏时,戈登离开现场。“佐伊对于我在场并不会觉得不舒服,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库梅尔觉得不行。”
库梅尔说:“我很抱歉。”
“没关系,你觉得怎样方便怎样来,我都行。”戈登一边说一边收拾她的东西,“现在我准备回家,睡一会儿或者玩会儿游戏。我真希望我丈夫每天都跟其他女人亲热!”
当戈登在芝加哥昏迷的时候,库梅尔有好几天都在逃避他父母的电话。终于有天晚上他接了电话,并承认他有了一个美国女朋友,而且不是穆斯林,现在生病中。“我只是觉得继续说谎太累了。”库尔梅说,他还以为母亲会暴怒,“但她冷静了下来,而且每天都会问我,艾米丽好点了吗?”然后当有一天他告诉母亲说好点的时候,她立刻转变态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2007 年 5 月,戈登出院。7 月,在六名朋友的见证下,她与南贾尼在芝加哥的市政厅结婚。两周后,南贾尼的父母在新泽西州举办了一场穆斯林婚礼。牧师以排外的态度,拒绝为任何有着非穆斯林名字的人举行仪式,所以那天戈登以伊曼这个名字出现。
南贾尼说:“我觉得那场婚礼是我母亲以另一种方式告诉艾米丽‘虽然你不是我理想中的新娘,但我在尽力把你纳入我们家庭’。”莎巴娜是南贾尼的母亲,她告诉我她对艾米丽的第一印象是:“我承认我有点失望,但慢慢地我开始像爱自己女儿一样爱她。”在穆斯林婚礼那天,莎巴娜把那件专门留给这个特殊日子的珠宝给了戈登。
南贾尼和戈登的结婚已经是一次越界。接着他开始跨越其他界线。2007 年春夏,他就自己与伊斯兰的关系写了一场 90 分钟的独角戏。8 月,他在芝加哥的湖滨剧场进行了演出。自那以后该剧场就关闭了,所以这部剧现存的唯一录像是一个像素很低的视频,但是记录的是首映夜的表演。
当时剧院的艺术总监是这样介绍南贾尔的:“最近几个月我们举办了许多精彩的演出,我们正在成为喜剧艺术的麦加圣地——帕顿·奥斯瓦尔特、詹尼安·吉劳法罗、玛利亚·本福德、路易斯·C·K 都在这表演过。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今晚即将出场的这位让我激动。”麦加圣地这个双关语看似并不是有意的。
这场演出的剧名是《难以言说》,来源于南贾尼踏上美国领土后的第一场对话,是他与拿着他护照的海关人员的一场对话。海关人员说:“欢迎来到美国..……先生,这太难以言说了。”不是“我不会读你的名字”或“你的名字怎么读”,而是“难以言说”。
现在南贾尼都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描述这场演出,而《大病》里恰好有段讽刺的独角戏。如果说《难以言说》在某些时刻有点少年读物的意味——比如对飘雪的描述过分讲究,但就整体而言,剧本是真诚而又深刻的,即使是在处理一些敏感话题,比如信仰危机与当众自我鞭笞的传统上,也是一样。
演出成了热点,也使得南贾尼与有名的经纪公司签约,并辞去了 I.T. 工作。戈登离开医院的五个月后,也就是 10 月,她和南贾尼搬去了纽约。南贾尼说:“并不像我们对彼此说的什么光阴易逝,让我们把握机会吧,但事后回想,艾米丽的病的确促使我们去审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

(图片来自 laweekly)
戈登终于结束了治疗,并和南贾尼搬去了洛杉矶,开始合作。他们共同主持了一档有关电子游戏的播客节目《The Indoor Kids》,和喜剧演员 Jonah Ray 成立了一档由戈登负责策划、几名固定演员轮换上场的周播相声节目,名为《The Meltdown with Jonah and Kumail》。从 2010 年到 2016 年,这档节目每周三在日落大道一家漫画书屋后面的小型黑匣子剧院进行演出,而这个地方刚好是酷宅文化中心的核心。
去年在洛杉矶时,我刚好赶上了最后一晚的《The Meltdown》,单口演员为阿帕图,音乐表演是一只讽刺支持川普的雷鬼乐队。表演结束后,南贾尼和戈登在现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和一些观众问好、拥抱。
戈登还写些个人文章、建议专栏和一本厚脸皮自助手册:《超我:释放内心的超级英雄》。她也会花大量空余时间给予建议。她在洛杉矶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喜剧演员,而喜剧演员很多时候,正如她所说,是“美好善良的人,但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如何像成年人一样生活”。她的一些朋友把她比作《彼得·潘》里的温蒂。
2013 年,南贾尼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拍摄一场一小时的单口相声特辑。这次他选择了自己的配乐——根据宝莱坞样本创作的说唱。在特辑《Beta Male》里,他在舞台上昂首阔步,即使他开玩笑说自己是懦夫或怪人。这场演出讲的是他的成长轶事。在 12 岁的那年,他在看一个被禁止的录像,当一个邻居频繁断电的时候,录像带卡在了录像机里。他想象自己羞耻地逃离走,接着还得照料自己:“需要帮工吗?我可以打败马里奥,也会画忍者神龟。”
表演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他看出观众席中有一名女性来自卡拉奇。
南贾尼在台上问她,卡拉奇现在如何了,因为自从大学后他再也没回去过巴基斯坦。
“老样子。”对方答道。
“还是经常有暴力冲突事件么?”南贾尼问道,还是带着感情的。
2012 年,南贾尼在西南偏南演出,在那里他遇到了阿帕图。“他开始跟我说他在芝加哥的日子。”阿帕图说,“我说,我觉得你那段经历应该拍成电影。”这就促成了接下来一系列会面、一封封邮件、一篇剧本草稿。四年后,《大病》诞生了。
南贾尼父母家中的场景是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拍摄的。去年夏天的一天,工作人员用假雪铺满屋前的草坪,南贾尼和戈登、修华特坐在客厅里,热烈地讨论着枪支政策。制片人孟德尔坐在后院的监视屏前面,因为房子的主人养了猫,而孟德尔对猫过敏。
“艾米丽父母的场景的拍摄过程比较正常。”南贾尼说。艾米丽的父母由霍利·亨特和雷·罗马诺扮演。
到我父母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父亲问他,应该由谁来演,他立即回答说,阿努潘·凯尔。凯尔一直都是宝莱坞的明星,而《大病》在他自己的计算,是他的第 500 部电影。当凯尔在道格拉斯顿拍摄的时候,南贾尼的父母坚持要来探班,这个画面让南贾尼感到紧张。
他走出房间在后院里踱步,说道:
现实世界和电影里的世界不应该靠得这么近,有些剧本上的东西我还没和父母讨论过。
那天早些时候,他们要拍一场库梅尔的母亲叫他去另一个房间做饭前祷告的戏。库梅尔展开祷告用的毯子,并在手机上设置了计时器,开始看视频、玩板球拍,五分钟后,他把毯子卷好离开了房间。
南贾尼的父母到了现场,和凯尔小聊了一会儿。父亲艾贾兹开玩笑说:“他看起来不就像是我出生时走散的双胞胎兄弟吗?”他们要求合影留念,大约十分钟后就离开了。一名工作人员对南贾尼说:“并没那么糟糕,对吧?”
后来我问他,婚后他与父母的关系进展如何,他说:“这需要过程,我觉得还不错。他们爱艾米丽,我们经常去探望他们。这很复杂。”他整理了下思绪继续说:“在电影里,库梅尔和他的父母还停留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第一步,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第四或第五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步要走。”
电影里,当艾米丽陷入昏迷的时候,库梅尔不知道如何联系她的父母。为了找到他们的电话号码,他必须要进入艾米丽的 iPhone。 他坐在病床边一边呢喃着“对不起”,一边将她了无生气的拇指放在手机的触摸板上,解锁了屏幕。当读到剧本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担心这一幕可能不够真实,因为看起来像是在电影里而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
当我在圣丹斯电影节上,与其他 1100 名观众坐在售謦一空的礼堂里,电影开始了。从片头开始,观众就沉浸在电影里了。在库梅尔被种族主义质问者打断后,艾米丽的母亲制止了质问者,她的独白引发了观众一阵中场掌声。初次与库梅尔共进午餐时,艾米丽的父亲就在开场抛出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对于9·11事件,你是什么立场?”库梅尔尖刻地回应道:“这是个悲剧。我的意思是,我们失去了19个顶尖好手。”——这引起了一波波大笑。
圣丹斯首演后,戈登在 Instagram 上发文:
我们刚刚进行了电影的首映。百感交集。
第二天,站在犹他州帕克城积雪皑皑的要道上,我请她描述其中几种情绪。“狂喜?震惊?恶心算不算情绪?”她这么说道,“当片尾字幕出现的时候,观众开始鼓掌,我的眼里都是泪水。我俯下身子,就像要解开安全带一样。怎么说呢,就像我的大脑真的坐了次过山车。”她推了推南贾尼,“他像往常一样没太大反应。”
“我只是不知所措!”南贾尼说,“那是我处理情绪的方式。”
一天之内,亚马逊就以 1200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大病》,这是圣丹斯史上最赚钱的一次交易。(在去年电影节上,亚马逊用 1000 万美金买下了《海边的曼彻斯特》。)从那以后,和南贾尼在帕克城散步就像在他的婚礼上跟着一个新郎。
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人们的头会转向他;他从未见过的人会跟他握手、拥抱。南贾尼的父母不断发信息告诉他很为他的成功激动。“他们还没看过电影。”他踌躇地说道,“不过他们会喜欢的。我觉得他们会喜欢这部电影的。”
四月份的时候,当我和他的父母谈起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看过电影。“但我们保持追踪电影评论和其他所有东西。”南贾尼的父亲说,烂番茄、IMDb、《Variety》、《好莱坞报道》都没有一个负面评价!
在圣丹斯,南贾尼抵达影人小屋,墙上有着仿古木镶板和麋鹿头。他是去那里和演员约翰·赵一起做个双人访谈。主持人提到他俩都出生于海外(约翰·赵来自韩国),并问道,对于成为“一个群体的代表”是否感到有负担。
“首先我想说的是,当我开始做单口喜剧的时候,人们对我有种族歧视,他们会叫我库马尔,我知道这肯定令人挺困惑的。”南贾尼说。他指的是 2004 年的喜剧《猪头逛大街》,这是一部有关一个印度裔和韩裔美国人进行了一系列醉后冒险的电影,也是没有白人主演但是最卖座的其中一部好莱坞电影。尽管南贾尼并没有出演这部电影,但陌生人经常叫他“库马尔”,所以他写了个相关的段子。
在南贾尼 2013 年的单口喜剧特辑里,他说:
我想出名,出名到成为流行文化的参考,人们就此进行种族歧视。这样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路人会说:“嘿,看看这个库梅尔·南贾尼。噢天,那真的是库梅尔·南贾尼!”
约翰·赵却是出演了《猪头逛大街》的,他饰演哈罗德。观众笑了,然后南贾尼很真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不会说,现在是改变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印象的时候了,这并不容易。我觉得只能是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如果能因此获得好结果那当然最好。”
![]()
(《硅谷》漫画)
比如在《硅谷》里,南贾尼的角色符合一些刻板印象,但也有一定的颠覆。他不时髦但坚持戴金链子,为此他经常受到嘲笑;他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他的死对头,一个来自加拿大的白人码农,却是一个非法移民。
亚历克·伯格,《硅谷》的联合制片人告诉我:
链子的主意来源于库梅尔的日常生活,包括申请美国签证的细节。当你尽力描述一个贴近现实的角色的时候,你会努力避免一些刻板印象,但你可以直接邀请库梅尔共进午餐,让他告诉你他的生活是怎样的,这太奢侈了。
访谈结束后,在后台,南贾尼继续了他对“全体代表”的看法。
人们用这些词太频繁了,频繁到开始变得没意义。但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你小时候看到的故事会告诉你什么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我快 40 岁了,当我看到新的《星球大战》里一个了不起的棕色人种演员时,我在电影院里哭了出来。
他继续说:
所有人都知道世俗的犹太人是什么样子,所有人都知道堕落的天主教徒是什么样子,流行文化里充满了这些。
但是很少有不是恐怖分子的穆斯林角色,很少有不去清真寺的穆斯林角色,很少有只是有着复杂背景但做着普通事情的穆斯林角色。当然,恐怖主义是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也需要一些去六旗公园吃冰淇淋的穆斯林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