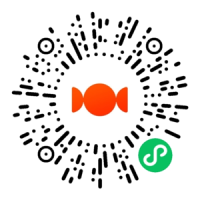超级富豪的末日准备
这是 ONES Piece 翻译计划的第 141 篇译文。本文原载于 NewYorker,作者 Evan Osnos,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 王沫涵、农颖、塔娜 翻译,关嘉伟 校对。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投和商业。
译者按:这是最坏的时代——人类仿佛正在经历着变幻多端的压力、挑战、矛盾与灾难。如果说我们能够相对轻易地感知普罗大众的焦躁与忧心,那么超级富豪这个神秘群体对此会有怎样的回应及态度呢?本文出自纽约客知名记者及作家欧逸文(Evan Osnos);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的超级富豪们不惜斥巨资做着周密的末日生存准备计划,深度剖析了「生存主义」行为的根源与发展,生动呈现了富豪阶层品行中的幽暗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阶级冲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适者生存」不可能再像它听上去那么轻巧了。
33 岁的史蒂夫·哈夫曼(Steve Huffman)是 Reddit 的 CEO 兼联合创始人,这家社交网络现在的估值已经达到 6 亿美元。在 2015 年 11 月之前,他还是近视眼,直到他做了一次眼部激光手术。哈夫曼决定做手术并非为了方便或者外貌,而是出于一个他通常不会谈及太多的原因——他希望治疗近视能让自己更有可能在自然或人为灾难中生存下来。「如果世界末日来了——或者甚至不需要世界末日,就比如我们遇到了什么危机——这时还要戴着眼镜就太麻烦了。」他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没有眼镜,我就是废人一个。」
哈夫曼住在旧金山,他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头浓密的浅黄色头发,神情中透露着无尽的好奇心。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时,他是学校交谊舞比赛的选手,喜欢恶作剧的他还曾经黑掉了室友的网站。相对而言,他不太关注具体会发生的灾难——无论是圣安地列斯断层发生地震、流行病爆发还是脏弹袭击,他更在意的是灾难过后的后遗症,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架构的暂时崩溃。」他说,「我有几辆摩托车,还有足够的枪支和弹药,以及食物。我觉得这些东西能让我在家里躲上一段时间。」
「生存主义」(survivalism),即为文明崩坏做好准备的行为,它通常会让人们联想到这样的画面:戴着锡纸帽住在森林里的人,囤积大量豆子的妄想症患者,虔诚的末日论者。但在近几年,生存主义开始向富裕阶层扩散,并在硅谷和纽约这样的地方扎根,影响着许多科技公司高管、对冲基金经理人和各个经济领域的顶尖人物。
去年春天的总统大选揭露了美国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为此,40 岁的安东尼奥·加西亚·马丁内斯(Antonio García Martínez),现居旧金山的前 Facebook 产品经理,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一座小岛上购置了五英亩植被茂密的土地,并把发电机、太阳能发电板和大量弹药带了过去。他对我说:「当社会失去了作为支撑的积极信念,它就会陷入混乱。」加西亚·马丁内斯写过一本言辞尖刻的硅谷回忆录——《混乱的猴子》(Chaos Monkeys),他想要一处远离都市但不与世隔绝的避难所。「人人都以为仅凭一个人就能搞定所有四处流窜的暴民。」他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需要组建一支地方民兵,还需要许多其他东西才能真正挺过一场浩劫。」在他开始跟自己在湾区的朋友们谈到这个「小岛计划」后,他们也站出来坦露了自己的准备工作。「我认为那些真正了解社会运行机制的人都很清楚我们现在正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
在一些私密的 Facebook 小组里聚集着一群富裕的生存主义者,他们在一起交流防毒面具、地堡和哪些地方不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等问题。其中一位成员是一家投资公司的高管,他告诉我:「我有一架时刻加满油的直升飞机,还有一个自带空气过滤系统的地堡。」他承认自己做的准备工作在朋友当中里算比较「极端」的,但他补充道,「我的很多朋友都准备了枪、摩托车和金币这些东西。这种做法已经不算罕见了。」
44 岁的蒂姆·程(Tim Chang)是风投公司 Mayfield Fund 的董事总经理,他告诉我,「硅谷里面有着这样一群金融黑客,我们会经常一起聚餐,讨论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生存准备。我们讨论的范围涵盖囤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如何在有需要的时候拿到第二本护照,在其他国家购置度假房产作为临时避难所。我也可以坦白说:我现在就在囤积房产,这不仅是为了增加我的被动收入,也是为了可以有避难的地方。」他和从事科技行业的妻子已经为自己和四岁大的女儿备好了逃离的行李。他告诉我,「我会想到这样的恐怖场景:『天啊,如果哪天爆发内战了,或者加州因一场大地震变得分崩离析,我们要做好准备才行。』」
马文·廖(Marvin Liao)是前雅虎高管,现风投公司 500 Startups 的合伙人。他也在为末日做准备,不过他认为只囤积食物和水是不够的。他问我:「如果有人过来抢这些东西怎么办?」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女,他说:「我虽然没有枪,但我有很多其他武器。我还去学了射箭。」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行为只是「纯爷们程序员」的娱乐,一种迷恋装备的现实科幻;但对于哈夫曼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悉心筹备了多年的事情。哈夫曼说:「自从我看了电影《天地大冲撞》(Deep Impact)之后,」这部 1998 年上映的电影讲述的是在一颗彗星撞进了大西洋之后,人们争相从海啸中逃生的故事,「每个人都想逃难,但是交通堵塞却让他们寸步难行。那个场景刚好是在我高中附近拍摄的。每次我开车经过那段路的时候都会想,我得买一辆摩托车,因为开车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哈夫曼是火人节(Burning Man)的常客——这场盛会每年都会在内华达沙漠举行,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商业巨头都能参与其中,他们在这里甚至不需要穿衣服。他尤其喜欢火人节的一条核心原则——「完全的自力更生」。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乐意帮助他人,但不希望请求他人」。生存主义者(有些会自称为「末日准备者」)认为 FEMA(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即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全称应该是「愚蠢地等待救援」 (Foolishly Expecting Meaningful Aid)。哈夫曼盘算过,当灾难来临之际,他应该会找到某种群体:「跟其他人在一起还是不错的。虽然这样说会显得有些自大,但我觉得自己应该会是一个好的领导。在危急时刻,我应该可以掌控大局,或者至少不会沦为奴隶。」
这些年来,哈夫曼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局的稳定,以及爆发大规模动乱的风险。他说:「当体制发生崩溃后,紧接着执行就会出问题。」(末日准备者的博客把这种状况叫做「W.R.O.L」,即「无法无天」(without rule of law)。)哈夫曼越来越相信,现代生活是建立在脆弱的共识之上的。「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正常运转,我们手中的货币是有价值的,权力会被和平地交接——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之所以能正常运转,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没问题。虽然我也认同它们抵御灾难的能力很强,而且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灾难,但我们以后要经历的灾难只会更多。」
Reddit 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成千上万个讨论组的社区,而且是全球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在经营这个网站的过程中,哈夫曼认识到了科技是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无论好坏。他亲眼目睹过社交媒体放大公众恐惧的方式。「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更容易感到恐慌,」他指出,「而互联网让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聚集。」 当然,它也能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危机。早在金融危机登上新闻头条之前,一些 Reddit 帖子的评论里面就出现了相关的迹象。「用户开始悄悄讨论房屋抵押贷款,担心学生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债务。许多评论说,『这事儿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一看就不对劲。』」他补充说,「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判断,但从整体上看,我觉得我们是反映公众情绪的有效标尺。如果社会要因为人们失去信心而崩塌,你会最先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根基的裂痕。」
可是,这种对世界末日的执念是如何在硅谷流行起来的?按照通常的印象,这里的人应该比谁都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才对。
这两种想法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实则不然。技术世界鼓励人们畅想各种不同未来的能力。罗伊·巴哈特(Roy Bahat)是旧金山风投公司 Bloomberg Beta 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容易会陷入无限的想象,最后到达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个极端。」 这种想象既可以产生绝对的乐观——比如人体冷冻术的风潮,人们选择在自己死亡后将尸体冷冻起来,希望未来的科技可以复活他们;也有可能会让人们看到凄凉的景象。时刻准备好逃难行李的风险投资人蒂姆·程告诉我,「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在乐观与惊恐之间不断摇摆。」
近几年,生存主义已经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之中。2012 年,国家地理频道推出了真人秀节目《末日准备者》(Doomsday Preppers),其中记录了各位参加者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的情况。节目在首集播出时就吸引了超过四百万观众,到第一季结束时,它成为了该频道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节目。一项由国家地理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40% 的美国人都相信储备物资或者建造防空洞会比 401k 养老保险更有投资价值。末日准备者在网上的讨论话题从相对正常的「妈妈在社会动乱时期应该怎么做」到更为恐怖的「怎么通过吃松树活下来」,什么类型都有。
奥巴马的连任推动了末日准备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极端保守派人士指责奥巴马政府加剧种族紧张关系、限制枪支自由和扩大国家债务的政策,他们会听从格林·贝克(Glenn Beck)和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等政治评论家的建议,在家里囤积各种冷冻干燥的农家奶酪和俄式牛柳丝。在一系列的「末日准备」展销会上,参会者可以学到伤口缝合知识(使用猪蹄来练习),还有机会与电视生存节目《生存与恐惧》(Naked and Afraid)的明星合照留念。
硅谷内部对末日的恐惧也有所不同。当哈夫曼在 Reddit 上关注金融危机的进展时,简彦豪(Justin Kan)第一次从朋友那儿大致了解到生存主义。简彦豪是游戏直播网站 Twitch 的联合创始人,后来这家公司以接近十亿美元的价格被亚马逊收购了。「我有些朋友说,『社会快要崩溃了,我们应该开始囤积食物。』」他说,「我试过这样做,但我们就囤了几袋米和五罐西红柿。如果真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死定了。」我问简彦豪,他的朋友们一般是怎么准备末日的。「大量的金钱和资源。」他说,「我还能担心或准备别的什么东西呢?这跟保险是一个道理。」
黄易山(Yishan Wong)是 Facebook 的早期员工,并在 2012 年至 14 年间担任 Reddit 的 CEO。他也为末日生存做了近视眼矫正手术,这样他就不用依赖眼镜这种「不可持续的外部援助来实现正常视力」。黄易山在一封邮件中告诉我,「大多数人都以为低概率的事件不会发生,但懂技术的人会从数学角度分析风险。」他继续说道,「科技圈的末日准备者们不一定认为末日就要来临,他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会在将来某天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考虑到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用其中小部分的资产对冲这种风险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到底有多少美国富人正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具体数字不得而知,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匿名是无价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在拒绝我的采访时这么说道。)有时,这个话题会在毫无预料之下被提及。LinkedIn 联合创始人、著名投资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回忆起有次他跟朋友说想去新西兰一趟,「哦,你是要去买『末日保险』吗?」这位朋友问他。「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里德告诉我。他后来发现,新西兰是人们购置末日避难所的胜地。霍夫曼说,「如果你说要在新西兰买房,这就相当于是一句暗号。一旦双方把暗号对上了,那么大家就会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我认识一个出售废弃洲际弹道发射井的经纪人,它们都做过了防核打击的加固,感觉住在里面挺靠谱的。』」
我请霍夫曼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硅谷亿万富豪已经购置了某种形式的「末日保险」,无论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我猜有一半以上。」他说,「但其实这就相当于买了一座度假别墅。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我想他们大可以说自己是在为自己害怕的东西未雨绸缪而已。」每个人害怕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但有很多人都在担心人工智能会蚕食新增的就业岗位,届时作为美国第二大财富聚集地的硅谷将会遭到强烈抵制(西南部的康涅狄格州是美国第一大财富聚集地)。「我已经从很多人那里听到过这个说法。」霍夫曼说道,「国家会跟富人作对吗?它会阻碍技术创新吗?这种情况会演变成社会动荡吗?」
另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 CEO 告诉我,「行业领袖们现在还没有到开诚布公地询问大家的末日计划的时候。」他继续道,「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适当谨慎的。」他提到了俄罗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络攻击,还有去年 10 月 21 日发生的黑客事件,后者导致北美和西欧发生了大范围的网络瘫痪,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体系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的食物供应取决于GPS、物流和天气预报。」他说,「而这些系统都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互联网又离不开域名服务器。当你逐一去了解各种风险因素时,你会发现很多因素是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然后你就会问,『这个东西在未来十年崩溃的概率有多少?』或者反过来:『未来五十年什么东西都不会崩溃的概率有多少?』」
生存主义变得流行的一个迹象就是开始有人站出来反对它。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是 PayPal 和借贷创业公司 Affirm 的创始人,他告诉我,「这是我为数不多不喜欢硅谷的地方之一——感觉我们是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我们即使犯了错,最终也能幸免于难。」
对于列夫琴来说,为末日生存做准备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他总是会在聚会上打断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通常会这样问他们,『你说你担心流浪汉的生活水平,那么你给你家附近的流浪汉收容所捐过多少钱?』我认为这种状况主要还是跟收入差距有关。所有其他形式的恐惧都是人为造成的。」在他看来,人们现在应当把金钱投入到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之上。「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很多人都会陷入困境。这时我们该怎么办?」
在美国的另一端,类似的尴尬对话也在一些金融圈子里展开。罗伯特·杜格(Robert H. Dugger)曾经做过金融行业的说客,后来在 1993 年成为了全球对冲基金都铎投资公司(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合伙人。他最近告诉我,「金融圈子里的人都认识一些担心美国会朝着俄国革命方向发展的人。」
杜格表示,他注意到人们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对抗这种恐惧。「大家知道唯一的真正答案就是解决问题。」他说,「这也是大多数人捐款做善事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投资各种各样的逃难方案。杜格回忆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场晚宴,当时正值「9·11」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过后:「一群百万富翁和几个亿万富翁在一起想象美国末日时的场景,讨论他们到那时会怎么做。大多数人会选择开飞机带着家人逃到西部的牧场或位于其他国家的住宅。」杜格说有一位宾客对此表示质疑。「他倾身问道,『你们要带上飞行员的家人吗?还有那些负责飞机维护的人呢?如果闹革命的人要闯进家门了,你们要带走多少跟你们有关系的人?』在他的不断质疑过后,最后大家都承认自己最后逃不掉。」
精英们的焦虑不会被政治阵营左右。即便是那些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指望他推行减税和放宽监管的金融家,他们现在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因为特朗普那些离经叛道的做法似乎会引起人们对现有建制的藐视。杜格表示,「媒体正在饱受其害。他们担心法院系统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们会不会从『假新闻』走向『假证据』?对于那些生计依赖契约精神的人来说,这就是生与死的问题。」
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A. Johnson)从同辈对逃难的谈论中看到了更深层的危机。59 岁的约翰逊拥有一头凌乱的银发,说话轻声细语的他总能给人一种和蔼而从容的感觉。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气工程和经济学学位,后来又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美国国会任职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进入金融业,成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的董事总经理。在 2009 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过后,他被任命为智库机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负责人。
不久之前,为了拜访约翰逊,我来到了他位于公园大道南(Park Avenue South)的办公室。他当时形容自己是一个意外了解到城市压力的学生。他在底特律郊区的格罗斯波因特帕克(Grosse Pointe Park)长大,父亲是位医生。他亲眼目睹过底特律在他父辈那一代衰落。「如今我在纽约看到的就像昨日重现一般。」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以前就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 Belle Haven。路易斯·贝肯(Louis Bacon)、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雷·达里奥(Ray Dalio)这些人(均为对冲基金经理)都是离我 50 码不到的邻居。我在工作上跟不少人交流过,越来越多人在说,『你必须要有一驾私人飞机,而且你要连飞行员的家人都照顾好。他们也得上飞机。』」
2015 年 1 月,约翰逊感受到了危险的信号:由严重收入不均引起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至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都开始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约翰逊对观众说道,「我认识一些世界各地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正在新西兰这样的地方购买飞机跑道和农场,因为他们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约翰逊希望富人们可以在金钱上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在面对政策变化时,比如更高额的遗产税,他们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25 位对冲基金经理赚的钱比全美国幼儿园老师加起来的还要多。」他说,「作为这 25 人中的一员其实也不好受,我认为他们变得更加紧张和敏感了。」贫富差距正在加剧。去年 12 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份新的分析报告,作者为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他们发现,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从 1970 年代起便与经济增长完全无关」。大约有 1 .17 亿人平均挣的钱和他们在 1980 年挣的没有差别,而最富有的 1% 的收入则翻了将近 3 倍。这个差距相当于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约翰逊说,「如果我们的收入分配更平均一些,有更多资金和精力被投入到公共教育系统、公园和休憩场所、艺术和医疗健康这些领域,那么社会上的问题将会被大大减少。但是大部分这些设施都已经被我们拆除了。」
随着公共机构的恶化,精英们的焦虑成了我们判断国家困境的一个指标。「为什么那些在别人眼中的权贵会显得如此恐惧?」约翰逊问,「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补充道,「这是令人费解的。你看到的这些最擅长预测未来、拥有最多资源,并因此创造了最多财富的人,现在却成为了最忙于准备带着降落伞跳下飞机的人。」
在去年 11 月初的一个清凉的傍晚,身处堪萨斯威奇托市的我租了一辆车,在夕阳中一路向北驶出城市。我经过了最后一座购物中心,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郊区,远处的地平线隐没在一片农田之中。几个小时过后,我在康考迪亚镇前转向西边,开进了一条两侧都是玉米和大豆田地的泥土小路。道路在黑暗中一直蜿蜒,直到我的车灯落在一座巨型不锈钢闸门之上。这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迷彩服的警卫,他手里握着一把半自动来福枪。
他领着我走了进去。在黑暗中,我能隐约看到一个巨大穹顶的轮廓,上面的金属防爆门正虚掩着。站在那里迎接我的是拉里·霍尔(Larry Hall),生存公寓项目(Survival Condo Project)的 CEO。这是一座 15 层的豪华公寓建筑,建于一个阿特拉斯(Atlas)导弹的地下发射井之中。这个设施曾在 1961 到 1965 年间存放过一颗被淘汰的核弹头。在这个原本为了抵御前苏联核威胁而建造的设施上,霍尔树立了一堵隔离新时代恐惧的围墙。「这里能让最有钱的人感到真正的放松」,他说「他们可以在这里随意走动,因为他们知道外边有武装警卫把守,可以放心让孩子们奔跑打闹。」
霍尔大概在十年前产生了这个项目的想法,他了解到联邦政府正在重新投资灾难规划,而这原本在冷战之后就鲜被提及。在「9·11」恐袭过后,布什政府启动了一项「可持续政府」(Continuity of Government)计划,用直升机和大巴将一批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运送到防御工事里面办公。但是在经过长年的荒废之后,地堡里的电脑和其他设备都过时了。布什下令重新关注可持续计划,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开始进行全政府范围内的年度演习活动。(最近一次是 2015 年的 Eagle Horizon 演习,当时模拟了飓风、简易核装置、地震和网络袭击的应急预案)。
「我开始想『等等,政府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霍尔说。2008年,他花了 30 万美元买下了那座发射井,并在 2012 年 12 月完成对它的改造工程,总共投资将近两亿美元。他在那里建了 12 套私人公寓:全层套间的标价为 300 万美元,半层套间的价格则减半。他说所有公寓都卖出去了,除了一间留给自己的。
大多末日准备者都没有这样的地堡,加固避难所的建造成本和难度都非常高。在被霍尔改建之前,这座发射井原本是美国陆军工程部为了抵御核打击而建造的。它内部储存的食物和燃料可供 75 人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生存五年。这里有用鱼缸养殖的罗非鱼,在生长灯下种植的蔬菜,加上可再生能源,这里可以一直自给自足,霍尔说。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的特警队装甲车(「Pit-Bull VX,装备有高至 50 口径的子弹」)会接上方圆 400 英里内的业主。有私人飞机的住客可以在 30 英里外的萨莱纳降落。在他看来,陆军工程部已经将最困难的选址工作完成了。「他们考察过这里的海拔高度、地震学研究记录,还有离大规模人口聚居地有多远。」他说。
爽朗健谈的霍尔虽然年近花甲,但仍然拥有十分健硕的身材。他曾在佛罗里达科技大学攻读商科和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进入了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哈里斯通讯公司(Harris Corporation)等国防承包商担任网络和数据中心的工作。他现在要经常往返于堪萨斯的发射井和他在丹佛郊区的家,他家里住着从事助理律师工作的妻子和他们 12 岁的儿子。
霍尔带领我穿过车库,走下斜坡,然后进入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有一个石造壁炉,旁边还设有用餐区和厨房。房间内摆放的台球桌、不锈钢家具、真皮沙发,给人一种置身于滑雪公寓的感觉,只是这里没有窗户。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霍尔参考了游轮的设计。与我们同行的还有马克·门诺斯基(Mark Menosky),他是这里的日常运维工程师。在准备晚餐时——有牛排、烤土豆和沙拉——霍尔说这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是维持地下的生活。他研究过如何避免产生抑郁(增加更多灯光)、预防形成派系(轮流做家务),以及如何模拟正常的地面生活。公寓的墙壁上装安装了多个 LED「窗户」,它们会实时播放发射井上方的草原视频。业主也可以选择播放松树林或其他景色的视频。一位来自纽约的意向住户想要看到纽约中央公园的视频。「一年四季,从白天到黑夜的景象。」门诺斯基说,「她还想听到那里的声音,比如出租车的鸣笛声。」
部分生存主义者指责霍尔这样做是在给富人建造一座专属的避难所,并扬言要在灾难发生时夺取这座堡垒。我在晚餐时向霍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挥手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们可以随意朝这里开火。」他说这里的守卫在必要时会开枪回击,「我们还有专门的狙击位。」
不久前,我跟泰勒·艾伦(Tyler Allen)通过电话,他是佛罗里达玛丽湖的一位地产开发商,他跟我说他花了 300 万美元在霍尔那里买了一间公寓。艾伦说他担心美国未来会面临一种「社会冲突」,政府会想方设法欺瞒民众。他怀疑埃博拉病毒就是为了荼毒民众而被故意引入国内的。我问他的朋友在听到这些想法时通常会有什么反映,他说,「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一笑置之,但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他继续说道,「不过我的担忧可是千真万确的。十年前,要是有人说我们国内会发生社会动荡、文化分裂、种族迫害和仇恨煽动,那他肯定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个疯子,但这些事情都确实发生了。」我问他在灾难发生时他要怎么从佛罗里达逃到堪萨斯。「如果一枚脏弹在迈阿密爆炸,大家都会躲进屋子里或聚集在酒吧内,一直盯着电视上的新闻。但其实你有 48 个小时来逃离这片鬼地方。」
艾伦告诉我,他认为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遭到了不公正的指责。「总统去戴维营避难不会被人说是阴谋论」他说,「但如果你有办法在灾难发生时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就会说你是阴谋论」。
为什么我们的反乌托邦情绪偏偏会在这个时候爆发?世界末日无论是作为预言、文学流派,还是商业机会都一直很有市场。它的影响力会随着我们的焦虑变得愈发强大。最早的清教徒移民来到美国这片广袤的原野大地时,他们眼里看到的除了天堂,还有末日的景象。1780 年 5 月,一片突如其来的黑暗笼罩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天空,农民们把这看成是一场预示基督回归的灾难。(事实上,这片黑暗是由安大略省的大面积野外火灾造成的。)劳伦斯(D. H. Lawrence) 生动清晰地描绘了美国人的恐惧。「毁灭!毁灭!毁灭!」他在 1923 年写道,「美国深邃黑暗森林之中似乎有什么在低语着」。
历史上,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沉醉总是发生在政局不稳和技术飞跃的时期。「19 世纪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小说,而每一本乌托邦小说都会有一本对应的反乌托邦小说。」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告诉我。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 1888 年出版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描绘了一个在 2000 年出现的社会主义天堂,这本书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以至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家「贝拉米俱乐部」。与之相对的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 1908 年出版的《铁蹄》(The Iron Heel)中,构想了一个在法西斯寡头统治下的美国,在那里,「0.9% 的人」掌握着「全国 70% 的财富」。
那时的美国人既惊叹于技术的发展——在 1893 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电灯的各种新应用让参观者们目瞪口呆——又在抗议工资过低、工作环境恶劣和企业贪婪的问题。「这跟今天的情况很相似」怀特说,「感觉当时的政治体系已经失去了控制,没法再处理社会的问题。那时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工人阶级奋起反抗,人们的平均寿命变短,让人觉得美国的发展已经到头了,整个国家将要垮掉。」
商业巨头们变得不安。1889 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即将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其身价相当于今天的 40 亿美元。他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阶级矛盾的担忧:社会阶层之间变得泾渭分明,他们在「互相无视」和「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下生活着。标准石油公司的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rfeller)是美国第一位身价上 10 亿美元的富翁,身为基督徒的他认识到了回馈社会的责任。「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所带来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退。」他在 1909 年写道,「因为人们最想要的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卡内基后来建造了将近 3000 座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创办了芝加哥大学。根据美国慈善学研究著作《基金会》的作者乔尔·弗雷施曼(Joel Fleishman)的说法,这两位企业家都致力于「从源头改变产生这些社会症结的系统。」
冷战期间,美苏末日决战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哈里·杜鲁门创立的美国联邦民防局发布了清晰易懂的说明文件,教导民众如何在核打击中生存下来 ,里面的内容包括「跳进最近的壕沟或排水沟里」和「永远不要失去理智」。1958 年,艾森豪威尔的希腊岛计划(Project Greek Island)破土动工,这是在西弗吉尼亚的群山之中建造的秘密避难所,里面可容纳所有国会成员。这座避难所隐藏在白硫磺泉镇的绿蔷薇度假村下方,30 多年来,这里一直为参众两院保留着备用的议厅。(国会现在也计划在隐秘的地方建造避难所。)当时美国政府还打算分别从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转移走葛底斯堡演说讲稿和独立宣言。
但在 1961 年,约翰·肯尼迪在一次电视演说中鼓励「每个公民」都参与建到辐射避难所的建设,他说「我知道你们不想做得更少。」1976 年,当时的美国人非常担忧通货膨胀和阿拉伯石油禁运问题,为了迎合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极右出版商库尔特·萨克逊(Kurt Saxon)发行了一份名为《生存者》(The Survivor)的时事通讯,里面介绍的是那些早已被遗忘的生存技能,它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萨克逊声称「生存主义者」(survivalist)这个词是他首先提出的。)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经济衰退和自我保护的书籍,例如 1979 年的畅销书《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坏年代变得富有》(How to Prosper During the Coming Bad Years),书中建议人们将金子以南非克鲁格金币的形式保存起来。这股「末日狂潮」在罗纳德·里根执政的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学家理查德·米切尔(Richard G. Mitchell, Jr.)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荣誉教授,他曾经花了 12 年的时间来研究生存主义,他说「在里根时期,我第一次从最高层政府官员那里听说——我现在已经 74 岁了——政府已经抛弃了我们,用集体制度来解决问题和理解社会的方式已经不管用。人们说,『好吧,制度确实是有瑕疵。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小布什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的不当处理让这项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前《时代》周刊记者尼尔·施特劳斯(Neil Strauss)是《紧急时刻》(Emergency)的作者,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转变为末日准备者的历程。他告诉我,「我们看到了新奥尔良的情况,政府明知灾难要发生,却无力拯救自己的公民。」施特劳斯在卡特里娜灾害发生的一年后开始对生存主义产生兴趣,当时有一位正在上飞行课和准备逃难计划的科技企业家向他介绍了一群「亿万富翁末日准备者」。施特劳斯取得了圣基茨岛的国籍,把自己的资产兑换成外币,并训练自己「在只有一把刀和一身衣服」的情况下生存。
近年来,每当朝鲜开始核试验时,霍尔的生存者公寓项目都会迎来一波咨询购买的高峰。但他指出了更深层的需求来源。「这个国家 70% 的人都不喜欢当前社会的走向。」他说。晚饭过后,他和门诺斯基带我到周围转了一圈。这座建筑的外形是一个高大的圆柱体,长得很像一根玉米芯,其中一些楼层被专门用作私人公寓,另一些则提供公共便利设施:有一个 75 英尺长的游泳池、攀岩墙、人造草皮做的宠物公园、一间陈列着苹果 Mac 台式电脑的教室、健身房、电影院,还有一间图书馆。这里会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而且不会让人感到局促。我们参观了一间军械库,里边装满了枪支和弹药,用于抵御外部人员的袭击。然后我们还来到了一间只有四面墙的卫生间。「我们可以把人们锁起来,给他们一些成人休息时间。」他说。总的来说,这里的规则由公寓委员会制定,也可通过成员投票修改。在危机时刻,也就是「事关生死的情况」下,霍尔说,每个成年人将被要求每天至少工作四个小时,并且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我们有出入门禁,由委员会管理。」他说。
公寓的「医务区」 设有一张病床、手术台和牙医椅。 霍尔说,「我们为住户配备了两名医生和一名牙医。」继续走上一层楼,我们来到了还没完工的食物储藏区。 他希望把这里的库存填满之后,它会变成一家「小型的全食超市」,但现在这里主要存放罐头食品。
我们走进了其中一个套间。里面有九英尺高的天花板、德国沃乐夫系列厨具和一个燃气壁炉。「这位业主想有一个来自家乡(康涅狄格州)的壁炉,所以他寄了一块用来造壁炉的花岗岩给我。」霍尔说。 还有一位来自百慕大的业主,他之前要求把自己公寓的墙壁涂成海岛风情的彩色蜡笔画(橙色、绿色、黄色),但他发现这些颜色在近距离看会让人感到很压抑,所以他只好叫装修师傅过来重新修改。
那天晚上,我在一间配有吧台和精致木橱柜的客房过夜,但这里没有之前提到的 LED「窗户」。房间里安静得可怕,让我感觉自己就像睡在一艘经过精心布置的潜艇里面。
第二天早上 8 点左右,我来到了公寓的公共区域与霍尔和门诺斯基碰头,当时他们一边在喝咖啡,一边在电视上看着《Fox & Friends》的选情新闻。那时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五天时间,身为共和党员的霍尔形容自己是一个谨慎的特朗普支持者。「在前面两场竞选演说中,我希望他的商业头脑能够压制他的冲动情绪。当看到特朗普和希拉里在电视上的选战时,他被特朗普支持者的规模和热情震慑住了。「我都开始不相信民意调查了。」他说。
他认为主流新闻机构的报道是有失偏颇的,他会认同一些其他人觉得难以置信的理论。 他主观认为「美国国会的有些做法明显是愚民政策」。我问他国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们不希望民众变得足够聪明,能够看清楚政治局势。」他跟我说他读到了一个估算,说 40% 的国会议员将会被逮捕,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一个与巴拿马文件、天主教会和克林顿基金会有关的阴谋,「他们对这件事调查了二十年。」他说。我问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当你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时,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但他并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
在我返回威奇托之前,我们参观了霍尔的最新项目——位于 25 英里开外的另一个导弹发射井,他正在那里建造第二座地下避难建筑群。当我们在工地边上停下来时,可以看到上方有一台起重机正从地下深处吊起建筑废料。这座新的避难所将能提供三倍的生活空间,部分原因是它的车库会被移至另一座单独建筑。新项目还会加入一些额外的设施,包括保龄球馆和跟玻璃落地门一样大的 LED 窗户,后者是为了提升建筑的空间感。
霍尔表示,他正在爱达荷州和德克萨斯州建造更多的私有地堡,还有两家科技公司请求他「为他们的数据中心和重要员工设计一座用于避难的安全设施。」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他已经在竞购另外四座导弹发射井。
如果你觉得位于堪萨斯州的避难所还不够偏远或私密的话,你还有另一个选择。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七天之内,总共有 13,401 名美国人到新西兰移民局登记,这是寻求居留权的第一个正式步骤——这个数字要比平时高出 17 倍。《新西兰先驱报》在报道这股移民潮时用了「特朗普末日」这个标题。
事实上,在特朗普获胜之前,这股移民潮已经开始很久了。根据新西兰政府提供的数据,2016 年的前十个月,外国人在新西兰购买了近 1400 平方英里的土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有余。美国买家的数量仅次于澳大利亚人。美国政府并没有登记在海外拥有第二或第三套房产的公民。正如以前的美国人会被瑞士的保密承诺和乌拉圭的私人银行吸引过去一样,新西兰提供的是安全和距离。在过去六年当中,有接近 1000 名外国人通过参与 100 万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而获得新西兰居留权。
新西兰广播公司 MediaWorks 的主席杰克·马修斯(Jack Matthews)是一个美国人,他告诉我,「我认为人们在暗地里会这样想,如果世界真的要完蛋,新西兰将是出逃的首选,这里在必要时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无论是能源、水还是食物。你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变差,但起码不会崩溃。」作为美国政局的远距离观察者,他表示,「新西兰和美国的主要区别在于,这里的人即使意见相左也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谈论问题。这个地方太小了,你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知道。所以这里的人还是比较文明的。」
奥克兰离旧金山大约有 13 小时的飞行距离。我在去年 12 月初来到这里的时候,新西兰的夏季才刚开始:天空是湛蓝的,20 多度的气温刚刚好,十分清凉干爽。新西兰群岛从南到北大概是缅因州和佛罗里达之间的距离,全国人口只有纽约市的一半。这里的绵羊和人口的比例是 7:1。新西兰在民主、廉政和安全方面都能排上全球的前十强。(它上一次遇到恐怖袭击是在 1985 年,当时法国间谍在这里炸毁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艘船。在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新西兰已经取代新加坡成为了全世界最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在我抵达后的第二天早上,格雷厄姆·沃尔(Graham Wall)开着他的梅赛德斯敞篷车来酒店接我,他是一位开朗的地产经纪,专门为高净值的人群服务。他的客户包括身价亿万的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沃尔没有想到,美国人之所以选择来新西兰,正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偏远。「新西兰人以前经常把『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挂在嘴边,」沃尔在开车穿过市区的路上对我说,「现在这反而成为了我们最大的财富。」
在这趟旅行之前,我还在想自己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参观各种豪华地堡之上。但是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新西兰建筑公司 Triple Star Management 的董事总经理告诉我,他的很多美国客户来到这里之后就觉得地下掩体是不必要的。「你不需要在门前的草坪下建一个地堡,因为这里离白宫有几千英里远。」他说。不过美国人会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当然,直升机停机坪是一定要有的。」他说。「你可以乘坐私人飞机前往皇后镇或瓦纳卡,然后你可以在那里转乘直升机,直接降落在自己的物业里。」美国客户也会咨询一些长远的建议。「他们会问,『新西兰的哪些地方在长期内都不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外国人对新西兰房产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引起了部分当地人的抵制,他们甚至发起了一个名为「反对外国人控制新西兰」(The Campaign Against Foreign Control of Aotearoa)的活动。其中来自美国的生存主义者是特别招人恨的一个群体。在末日生存者网站 Modern Survivalist 上有一个讨论新西兰的帖子,下面有人留言写道,「美国佬,你们给我听着,新西兰不是你们最后的避风港。」
一位 40 多岁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最近在新西兰购置了两处房产,并获得了当地的居留权。他同意在不公开姓名的前提下向我分享他的想法。在美国东海岸长大的他拥有高大健硕的身材和晒得黝黑的皮肤。他喝下一口咖啡告诉我,美国将面临至少十年的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紧张、两极分化和人口迅速老龄化。「这个国家已经分成了三个地方——纽约地区、加州地区和其他地方,因为纽约和加州以外的地方的贫富悬殊十分严重。」他说。他担心如果美国政府草率地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注资的话,国内经济会受到损害。「政府能履行这个承诺吗?还是会直接给有需要的人印钞票?这样做会对美元价值造成什么影响?这不是明年就会发生的问题,但也不是五十年后那么遥远。」
在对冲基金经理的圈子内,新西兰俨然已经成为了末日避难的首选,所以他并不希望将自己跟那些更早一步来到这里的人混为一谈。他说,「在担心世界末日的已经不再是少数怪人了。」他笑着说,「除非我也是这些怪人之一。」
自 1947 年以来,《原子科学家公报》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由曼哈顿项目成员创办的一本杂志) 每年都会邀请一批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名人,让他们一起讨论并更新「末日时钟」的读数,这是一个形象地反映文明覆灭风险的仪表。到了 1991 年,随着冷战结束,科学家们将末日时钟调至有史以来最安全的时刻——「午夜」前的 17 分钟。
从那以后,时钟的指针又开始向末日逐渐逼近。2016 年 1 月,当时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加剧,而且地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因此《公报》将末日时钟设为午夜前 3 分钟,也就是跟冷战局势最严峻的时刻相同。同年 11 月,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该小组再次召开他们的年度保密会议。如果他们选择将时钟的指针向前移动一分钟,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达到了自 1953 年以来最高的末日风险,当时美国刚刚完成首次氢弹试爆。(根据今年 1 月 26 日公布的结果,末日时钟现在的时刻是午夜前两分半钟。)
如果对灾难的恐惧可以促使人们采取预防措施话,那么它就是有益的。但是精英们的生存主义不是预防措施,而是一种退缩行为。美国的慈善事业支出仍然是全球最高的,其 GDP 占比是第二位的英国的三倍。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可能要把头号慈善大国的位置让出去了,因为美国最富有的人群中的一部分已经减少了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在看到美国衰退的征兆,看到他们曾经受益其中的制度和规范开始崩溃时,他们已经开始想象可能的失败。这是一种镀金的绝望。
正如 Reddit 的哈夫曼所观察到的,技术让我们对风险更加警觉,但也使我们变得更加恐慌;技术促使我们作茧自缚,将自己与敌人隔绝开来,同时不断加深我们现有的恐惧,而不是鼓励我们去击破恐惧的源头。没有积极为末日囤积食物的科技投资者简彦豪告诉我,他想起有一位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朋友最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们应该在新西兰购置土地作为退路。他当时的原话是,『特朗普实际上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的可能性是多少?也许很低,但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期望值是很高的。』」
其实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缓解当代的末日焦虑。「如果我有十亿美元,我不会用来买一个地堡,」数字医疗初创公司 Neurotrack 的 CEO 艾利·卡普兰(Elli Kaplan)告诉我,「我会将其重新投入到民间团体和民间创新上。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想出更聪明的方法来确保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卡普兰曾在比尔·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工作过,她对特朗普的胜选感到十分震惊,但表示这在另一方面也是对她的一种激励:「即使处于最深的恐惧之中,我仍然觉得,『我们只要联合起来就能战胜它。』」
这个观点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信心——相信即使是退化的政治制度,它们仍然是集体意志的表达方式,是形成和维持我们的脆弱共识的工具。相信,也是一个选择。
硅谷导师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是一位作家和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称他为自己的灵感来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兰德出版的《全球概览》以其糅合嬉皮士和极客精神的内容吸引了一群狂热的追随者(它的座右铭是:「我们已经成为了神,也许我们也能当好这个角色。」)布兰德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告诉我,他在 1970 年代就研究过生存主义,但不久后就放弃了。「总的来说,我发现『天啊,这个世界将要分崩离析』这样想法很奇怪。」他说。
77 岁的布兰德住在旧金山北面的小城索萨利托(Sausalito)的一艘拖船上,比起世界脆弱的一面,他更愿意看到它的抗打击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世界撑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而且没有引起社会暴动;埃博拉病毒在没有造成大规模感染之前就被战胜了;日本在经历过海啸和核危机之后仍然没有倒下。他认为,美国人正在退缩到经验为上的小圈子里,这样会损害「同理心的大圈子」,也就是让人们停止为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我要怎么保护我和我的财产?这种问题是很容易想到的。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文明能够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一直延续下去会怎样?如果它可以一直蒸蒸日上,我们该做什么?」
在新西兰停留了几天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同时逃避上面的两个问题。一天早上,在奥克兰蔚蓝的天空之下,我和 38 岁的美国人吉姆·罗尔斯塔夫(Jim Rohrstaff)一起乘上了一架直升机。在密歇根州上完大学后,罗尔斯塔夫成为了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后来在豪华高尔夫俱乐部和地产行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乐观自信的他拥有一双湛蓝的眼睛。在两年半前,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新西兰,他的工作也变成了向「高净值人群」销售房产,他说他们都是想要「远离世界所有问题」的人。
罗尔斯塔夫现在是精品地产中介 Legacy Partners 的合伙人。他想带我去看看 Tara Iti,这是他们新建的高档住宅和高尔夫俱乐部项目,主要面向美国客户。直升机向北穿过海港和海岸,一直飞到城市外围的茂密森林和田野。从上空俯瞰下来,大海显得无比浩瀚,在海风的吹拂下掀起了粼粼波光。
直升机缓缓降落在高尔夫果岭旁边的绿色草坪上。这个新建的豪华社区将拥有三千英亩的沙丘和林地,还有七英里的海岸线,但是只设有 125 户住宅。罗尔斯塔夫开着一辆路虎带我参观这个项目,他向我强调了这里的隐蔽性:「你在外边是看不到这里面的任何东西的。这对公众和我们来说都更好,也是为了保护住户的隐私。」
当我们接近大海时,罗尔斯塔夫停下路虎,穿着他的懒人鞋走下了车。他带着我走过沙丘,来到了一片延绵不尽的海滩,我在这里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汹涌的海浪不断拍打着岸边。他张开双臂,转过身来大笑道,「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生活的地方。」这是我在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没有想到特朗普,或者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