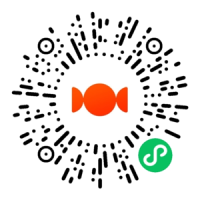反乌托邦(文学和电影)这种廉价的兴奋可行,至少能娱乐人,能卖票。
Manu Saadia 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很艰难的时代。
一方面,曾被认为能为人类带来更平等生活的科技,现在却呈现出多种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气候等环境问题也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很多时候也难以乐观起来,因为文学和流行文化中也充斥着反乌托邦科幻作品,平常人更难去想象一个乐观的将来。

Saadia 是书籍《Trekonomics: The Economics of Star Trek》的作者,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对反乌托邦小说的支持和消费,让这种主题泛滥到让人觉得疲惫。
每天,超高预算制作的噩梦都陪伴这我们经历这个让人不满的世界。从《疯狂的麦克斯》到《饥饿游戏》再到《黑客帝国》,它们都呈现出一个典型的沦陷的未来。
这当然特别好营销,因为它们代表了最古老的神话 —— 人类的衰败。这个故事在看似有无数种变体的情况下不断被重复述说和复制。
反乌托邦这种廉价的兴奋可行,至少能娱乐人,能卖票。

和反乌托邦某种程度上的「千篇一律」相比,乌托邦这种要去主动构思创想一种更乐观的世界却要求对现实生活拥有主动的思考。
Saadia 指出,乌托邦文学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最开始是社会评论的诗意表达。当时的政治理论家开始探讨社会的结构和意义。譬如,William Morris 就通过《News From Nowhere》构建出一个后工业时代社会,讲述一种当城市边界消失,一切资源平等的可能性。
乌托邦文学最鼎盛时期当属 19 世纪,而从那之后就将近消失了。有趣的是,如果要在现代生活中寻找乌托邦主义,我们也许能在城市规划中找到稍微浅薄的乌托邦构想 —— 可持续发展商业区、漂浮的城市构想,还有移居到火星以及月球的计划。